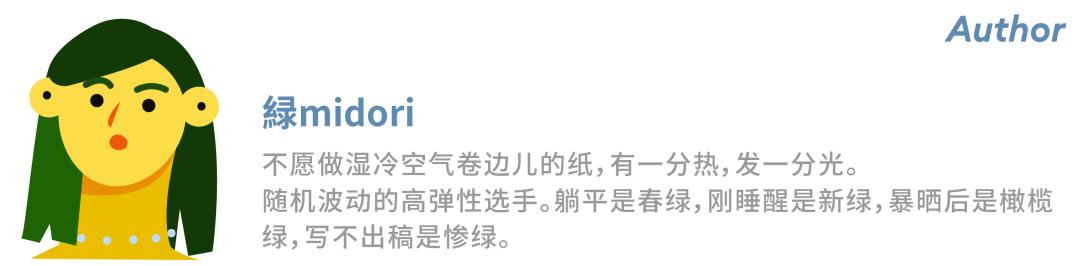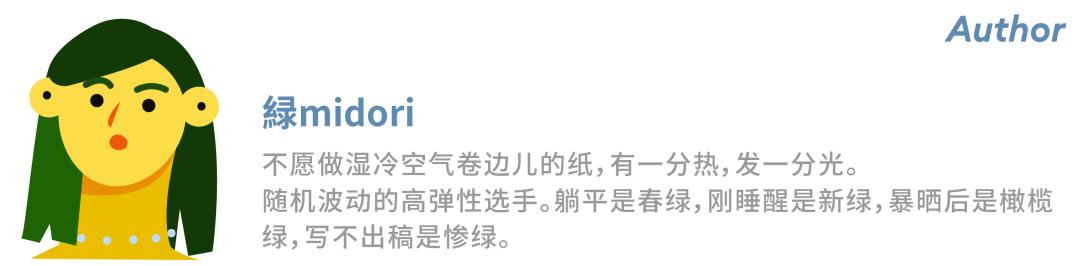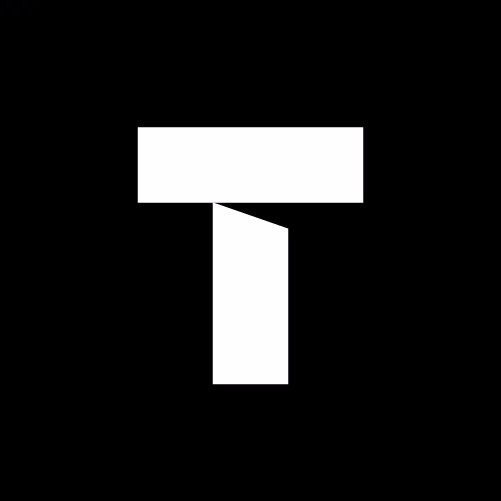“从前面的石拱门进去,到老街直走,过桥后右转就到了。”司机指路时寥寥几句描绘,才让我真正有了已经来到乌镇,来到乌镇戏剧节的实感。这是一种在智能导航语境中失而复得的熟悉感:没有中庭,没有灯箱,没有现代门牌,有的只是石街,廊桥,亭榭,支护窗,和青团一样碧绿又轻轻弹动着的河流。乌镇戏剧节已经走到了第十年。尽管依然有人对场景营造中的“人工感”抱有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被忘却在日常之外的事情,也依然只能在此地中发生。这份“唯有此地”的特别,造就了乌镇环境戏剧的创作基因:2014年,赖声川、黄磊、陈明昊便在乌镇白莲区的两栋古宅里制作了环境戏剧《梦游》,以昆曲为引,古代女子与两位作家的不同邂逅为线,以中式园林的回环曲折、人景合一的动线设计为轴,引领观者游走于梦境、戏剧、现实的边界。在国内首档戏剧类真人秀《戏剧新生活》里,导演丁一滕也以乌镇水剧场为背景,重新改编了王尔德经典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结尾两位演员一同跃入了新月形湖泊之中,用飞溅而起的水花带彼时被困住的我们,重新审视了“在场”的意义。环境戏剧(Environmental Theatre),顾名思义是对演出场所的拓展,主张生活中的一切场景皆可成为“舞台”。它先锋,但并不小众,甚至远比想象中“泛滥”——在很多艺术事件、地产造节上,关于“环境戏剧”的宣传屡见不鲜。但戏剧该如何表征环境?或者说在空间这一块巨大的幕布上,如何抓住最动人的那些星星点点让它成为戏剧?也许这才是在给戏剧赋予一种开垦商业价值的功能之前,更应明确和坦白的问题。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主题为“起”,意为跃起、奋起、迎风起飞,迈向新的旅程。汇聚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戏剧集市五个单元,特邀剧目名单又分为“大师佳作”“文学舞台”“经典新排”“当代先锋”“舞蹈剧场”“环境戏剧”“学院观察”七大版块,11天时间、12个剧场悉数开放。
“从前面的石拱门进去,到老街直走,过桥后右转就到了。”司机指路时寥寥几句描绘,才让我真正有了已经来到乌镇,来到乌镇戏剧节的实感。这是一种在智能导航语境中失而复得的熟悉感:没有中庭,没有灯箱,没有现代门牌,有的只是石街,廊桥,亭榭,支护窗,和青团一样碧绿又轻轻弹动着的河流。乌镇戏剧节已经走到了第十年。尽管依然有人对场景营造中的“人工感”抱有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被忘却在日常之外的事情,也依然只能在此地中发生。这份“唯有此地”的特别,造就了乌镇环境戏剧的创作基因:2014年,赖声川、黄磊、陈明昊便在乌镇白莲区的两栋古宅里制作了环境戏剧《梦游》,以昆曲为引,古代女子与两位作家的不同邂逅为线,以中式园林的回环曲折、人景合一的动线设计为轴,引领观者游走于梦境、戏剧、现实的边界。在国内首档戏剧类真人秀《戏剧新生活》里,导演丁一滕也以乌镇水剧场为背景,重新改编了王尔德经典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结尾两位演员一同跃入了新月形湖泊之中,用飞溅而起的水花带彼时被困住的我们,重新审视了“在场”的意义。环境戏剧(Environmental Theatre),顾名思义是对演出场所的拓展,主张生活中的一切场景皆可成为“舞台”。它先锋,但并不小众,甚至远比想象中“泛滥”——在很多艺术事件、地产造节上,关于“环境戏剧”的宣传屡见不鲜。但戏剧该如何表征环境?或者说在空间这一块巨大的幕布上,如何抓住最动人的那些星星点点让它成为戏剧?也许这才是在给戏剧赋予一种开垦商业价值的功能之前,更应明确和坦白的问题。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主题为“起”,意为跃起、奋起、迎风起飞,迈向新的旅程。汇聚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戏剧集市五个单元,特邀剧目名单又分为“大师佳作”“文学舞台”“经典新排”“当代先锋”“舞蹈剧场”“环境戏剧”“学院观察”七大版块,11天时间、12个剧场悉数开放。暌违已久的世界级剧团回归: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带来的开幕大戏《H-100秒到午夜》,以霍金对宇宙和人类的口吻为线索,展现了精准、冷峻的独特美学。OG剧团的《倒行逆走新世纪》,以回文诗般、视觉隐喻的方式展现了人类走向衰亡或救赎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也很感兴趣,十年了,“乌镇”的故事还能怎么讲?今年的“环境戏剧”板块,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赖声川导演的《长巷》,孟京辉导演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以及波兰行者无疆剧团的《欧律狄刻》。而《长巷》作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剧目,开售即被黄牛炒至天价,现场排队六小时依旧“一票难求”。能够吸引普通观众的,当然不是“环境戏剧”这个概念。因为赖声川,也因为乌镇戏剧节。即便它又新又定制化,事先不可能有任何推荐;你也能想象到,前者会给出一个满怀深情的本子,而后者会兜住你想要在此入戏的某种热忱。《长巷》是赖声川导演为乌镇创作的新作,10月25日首演,共演6场。长巷确有其巷,是沈家戏园旁边的洪昌弄,长80米,宽仅1.5米,若非想抄小道,掠过并错过毫不意外。而这条极限小道,便是《长巷》的舞台,也是其叙事主体。在这里,观众从舞台之下的上帝,变为一个古镇的闲散路人,分A/B两组在巷子首尾汇合,穿过洋行、洪昌巷,再随着剧情中演员的相遇,来到沈家戏园的旧椅上。进入长巷,人便成了环境里的一块拼图,已然入戏。为了让故事的主角更顺畅地成为一个被聆听、被凝视、被跟随的角色,导演将其身份设定为了一个“导游”,而观众则是跟随他途经此地的游客。他们像是偶然闯入般,目睹了一个老去的人和年轻的自己对话,聊盆栽、聊桂家姑娘、聊种种“知来者不可追”的幸福时刻。这“小”得如此顺利成章: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石板路上没有传奇,个体即是一个不停旋转的支点,和巷弄里的生活一样小而踏实。环境戏剧击碎了舞台,把演员和观众都放进同一条巷子里。剧本不再是绝对权威,正如如果下起雨来,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被淋湿。演员的讲述不再受制于等待幕布和道具组,观众也有了更多互动和观察的机会,即便被空间里的其他东西分掉了注意力也没关系,因为或许你赢得的是一种去塑造故事的主动权。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重要,但答案可以是一切。要让戏剧替环境开口说话,它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对于环境的、有情感的理解之上。“环境戏剧之父”、美国戏剧理论家理查·谢克纳认为,戏剧并不仅限于舞台上的表演空间,以政治的观点看,它可能是一个“立场”;以学者的观点看,它可能是一个“知识体”;以戏剧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德国著名戏剧理论家汉斯-蒂斯·雷曼也在《后戏剧剧场》里说过,“剧场演出也可以看做是演员与观众共同度过的一段真实时间。”一个称之为“环境”的地方,必然有空间作为实际的载体,譬如一条巷子,一个酒店,一间废弃的车库。而它得以成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则在于它除了“舞台”之外还有别的、可被利用的空间功能,人们带着对它情感或陌生的探知欲走进这里,再让猜测一一实现或落空。因此,这里如果要发生一场戏,要么是一段真实或者可能真实的故事,要么是一个与一草一木有所牵连的延伸——简而言之,它和空间的存在逻辑,以及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我想在此引入前几天在乌镇街头听到的一句“无心之语”。嘉年华表演是乌镇戏剧节的一部分,走在西栅大街上,你会偶遇很多似乎刚从童话、传说以及某个断代中走出来的人物。这群不期而遇的奇幻客人,骄傲地走在路上,奏琴、跳舞、变魔术、踩高跷,使出浑身解数和路过的人们互动。一个极其大胆的小朋友,凑到女演员的眼皮底下,像照镜子一样学着对方的动作。表演结束后,她还延续着刚学那几招,在路上旁若无人的律动着,旁边一位妈妈一样的人大笑着说:“囡囡,你别太入戏喏啦!”一语道破——在我们的广袤的土地上,气质温润的江南水乡可以有很多个;但引人入戏,则是乌镇作为一个环境的独特性。于是在环境里衍生出这样的共识:我们可以并且被鼓励在这样一个在有历史,有过去的建筑群里,相谈一些如梦似幻的事。没有人会因为《长巷》里“与自我相遇”这个设定,就把它打成一出魔幻大戏,它依然平实且小,因为在乌镇的环境里,这种程度的“魔法”发生,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正因如此,我和所有人一样,都不认为“错过这次,还有下次”,无论是故事设定的背景、演员行走的动线、还是一种江南的哀愁,似乎都独属于此地。《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利用了枕水雕花厅略带奢华的场景去讲一个爱上赌徒的故事,非常合理;《欧律狄刻》利用了水剧场开阔、环水、观众能随之移动的特性,让观众从不同角度去观赏一场美丽的离别,同样合适——但优秀的置景师们完全可以利用高超技术,更换一些你看不出的角度,将其迁移到别的城市、类似的场景里去,省掉那些必须“此时此地”的遗憾。大概看到这里,你已对“环境戏剧”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作为普通观众,模糊即是最好的状态)。它不再是传统的展演关系:演员在台上,观众在台下,中间隔着一个庞大、尖锐、但评论家老是让你忘掉的舞台,演员用信念感讲一个遥远的故事,而观众负责远远的凝望、适时的流泪或欢笑,最后再以掌声与此作别。它不去打破第四堵墙,因为本没有墙。而在近些年的环境戏剧中,关于“墙”的替代场景,大概有几个方向:自然(能和市集消费及自然主义生活方式所衔接的场景)、社区/街区/小型生活空间(与空间功能结合较为紧密的“附近性”场景)、老厂房/旧车间(切中城市更新议题、完成空间活化的场景)。当文本不再是绝对权威,甚至没有文本,“戏剧”本身的逻辑就被观众抛在了“环境”之后。主办方省下了一笔不低的场地费,同时也省去了漫长的教育成本。而戏本身的质量,除了创作人员本身,亦取决于将“驻地”作为创作方法时,固定成本和感性因素的投入。面向市场时,它似乎有另一套创作及衡量投入产出比的方法。
谢克纳曾说,中国传统戏曲中,早就有环境戏剧的影子,而向环境戏剧转向的动机,则顺理成章地激活了我们文化中原本就有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留存于我们文化共识中的原因,而“当下”的迫切,则对应着我们经历了三年“流通闭塞”产生的真实焦虑。如何在失重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坐标?如何确信我们以一种有未来的状态活着?毫无疑问,这是如今或者更长期,我们将主动或被动地思考的问题。“戏剧”本身,无疑是一种接近于早期“巫术”的形式,具有疗愈性质,同时以非日常的仪式来模仿神、接近神、以期超越自身有限性。而环境戏剧,又进一步跳脱了“镜框”,重新放大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间以及我们本身,使得人可以找回一种稀缺的“在场感”、重新把握主动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并非是市场捏造了这一需求,而是在合适的时间,它终于走到了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