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 0
- 1
分享
- AI与未来千年的艺术
-
原创 2023-09-12

1
绘画死了吗?
1839年,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惊呼“绘画已死”,只是缘于他看到了一幅版画。他从中看到了某种和杜尚类似的视野——后者选择遁入现成物艺术的世界。然而,绘画(包括严格意义的架上画)并没有死亡,摄影术、印刷术只是稀释了绘画中某些细分领域的估值——如摄影般的绘画。另一方面,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绘画却在19世纪末应运而生:某个火山忽然受阻熄灭了,岩浆却从意想不到的另一处喷发而出。
公元868年,全球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出现在敦煌。这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不通过手与笔即时生产,而是通过一套装置组织化的批量生产图像和语义符号,德拉罗什看到的欧洲版画只不过是这一工具的历史延伸。
2023年8月23日,美国一位地方联邦法官驳回了一项颇具争议的申请——AI 生成艺术品《最近的天堂入口》的版权申请。据报道,法官认为这件作品是由 AI 自主“创作”完成的。法官豪威尔(Beryl A. Howell)根据先前的判例认为,版权的前提是人类作者身份,泰勒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最近的天堂入口》(2018)无法证明人工智能机器参与创作的程度,自然也就无法证明这幅作品是完全由人来创作的。泰勒在其他国家也没能为自己的 AI 创作作品争取到版权。

斯蒂芬·泰勒(Stephen Thaler)《最近的天堂入口》 2018
对比这三个例子,从木头到硅基,图像和语义生产的本质结构(人-工具)存在事实上的改变吗?为什么我们会下意识的质疑AI取代了创作,而不质疑使用雕版印刷金刚经的中国古代出版者呢?大概是由于第三个案例中,机器看上去具有更多的“自主性”。
依照图灵的标准,后工业时代的AI似乎足以通过人机测试,从而拥有人格化的著作权。然而,艺术史中,生产资料的制造商从不会与作者相混。当我们讨论杜尚的小便池时,不会觉得是洁具商Mutt创作了《泉》。一个人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全由AI制造并非是不能接受的。艺术品并不必然是人造物,更不需要是艺术家本人所制造的。毋宁说,艺术品是由艺术家的工作所揭蔽的。
因此,在英美法体系中的这个判例,仅仅意味着人与AI版权博弈的开端。德拉罗什的惊呼已将近200年,绘画并没有死,艺术家——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画家———也并未凋零。贡布里希提示我们,三万两千年来,作为艺术家意味着多重身份,但没有一个身份是工匠。在原始洞穴中他是一个巫术的发动者;在古埃及他是一个书记员,负责重大事件的记录;在古中国他是一个文官,承载公共空间的营造。图像生产,仅仅是整个系统中最后的一环,处于最浅表的位置,或许由底层工匠完成,而居于核心的是表达自由意志的关键人物:第一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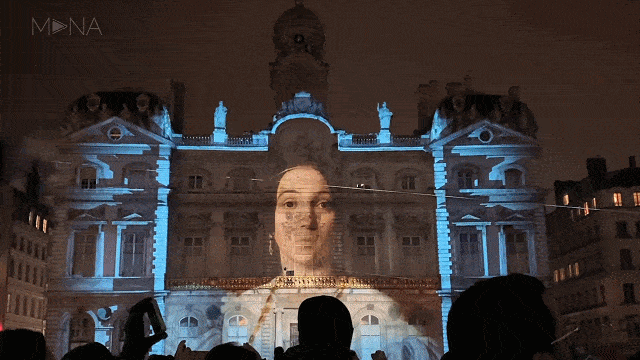
来自法国的Inook成立于2000年。创作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Deepfake让博物馆中几个世纪前的肖像画“活了过来”,演绎流行歌曲,算法重新创建了面部的体积和动作。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文艺复兴的大师工坊中屡见不鲜的事实:学徒与大师的作品经常混淆,学徒帮助大师生产,并以大师的名义完成订件。大师的组织化生产中,学徒是他的工人,而所有工具是他的生产资料,除大师本人外,所有要素都是可替代的。在极端的例子中,甚至连大师本人的肉体也是可替代的,例如丢勒的版画由一个超过100人的团队创作。
历史上第一个知识产权案例也由丢勒控诉他的抄袭者马肯托尼欧·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而产生,毕竟,丢勒的学徒可以代劳,那么其他工坊理论上也可取而代之。雷蒙迪的惟妙惟肖引起了丢勒的恐慌,然而,即便雷蒙迪完全通过自己的手作完成版画,也不能够说他是独立创作的。荒谬的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艺术家在模仿(抄袭)他人的时候尚且不敢公然宣称自己是“第一作者”,而今天我们却在慎重其事的考虑一个并不具有自由意志的AI成为第一作者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有针对性的自由意志的初始力量,更进一步地说,这个力量也是启动同一针对性的自由意志的初始因素。

(左)圣母生平 第8幅 丢勒 约1504
(右)圣母生平 第8幅 赝品 约1505
这意味着围绕大师所营造的艺术生产,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价值,它是难于复制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套可转录的编码(只不过需要极高的成本)。这种艺术生产能力,我将之称为“精神力”(Spiritual Power):一种目前仅由人脑对图像及符号系统的特殊的创造及感知能力,它是一种支配人类生活得以继续下去的无法企及的客观存在。
值得指出的是,在人脑的这种特殊功能中,首先是感知,而后才是创造。虽然丢勒或他的版画工坊创造了《忧郁》系列,但没有人竟至于能够欣赏或看懂,那么就会遭遇传播上的困难。事实上,丢勒是繁盛于纽伦堡的,他的版画叙事中夹杂着许多流传在德语区的圣经画面,为他与他的读者所激赏。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将这种理解过程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罗兰·巴特也在此意义上宣告了作者之死和读者之活。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艺术的生命取决于读者而非作者,读者不死,则与之相关的艺术史不会死亡。这时我们可以强调,那个“支撑人类生活得以继续下去的无法企及客观存在”潜藏于人类的任何一员的感知中,正是读者或者观者在激活和加强作者的感知及其感知的符号象征。

《忧郁I》丢勒 1514
2
何为本体?
一套发射和接收装置,在贡布里希看来,艺术史必定是由这两者功能构成的。画家发射出某种图像或语义符号;观看者的义务,在于他需要调准频道,达成感知-创造的精神通道。现在,追随者、伪造者和AI都对这种符号系统加以模仿,理论家则试图加以解构。
沃尔夫林早已发现,对视觉要素做结构分析可以获得丰富的结论。他的五对概念(线描和涂绘、平面和纵深、封闭与开放、多样性与同一性、清晰性与模糊性)的工具箱成为艺术史必备的知识准备之一,然而这五对概念却无法界定一件作品杰出与否。正如AI的工具箱,当你企图将体验转换为语言时,或拆分为语义系统,那么就面临着体验的肢解。体验,就其不断的整体流动而言,在某一瞬间可以输出为一个文本,而在另一个瞬间可以输出为另一个文本。文本正如体验的影子。模仿影子的高手并不能回到本体,除非我们一开始就面对本体。一件杰出的艺术品是作者的文本与他的体验及其终极意图正好高度契合的结果。

中国艺术家刘思辰用AI山海经构建了一个纯粹虚构的图景——计算机基于动物图鉴生成的虚拟生物被放进人工拼凑成的场景中。
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是关于猴子的(Infinitemonkey theorem):一只猴子可以在打字机上打出莎士比亚全集(只要时间足够)。这个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猴子随机打字能够打出与《哈姆雷特》第一个字母相同的概率为1/26,第二个字母也要相同的概率为1/676。这里概率显然发生了指数爆炸。可以想见,猴子打出哈姆雷特需要天文数字级别的尝试。
这个思想实验正确的看到莎士比亚全集是一个语义符号系统,但许多人仅仅看到这一点,就此推断:由于难以被猴子随机打出,莎士比亚拥有巨大的价值。但是,这个仅仅基于概率的理解是不充分的,文学的价值与文本的长短无关。否则,一千万字的网络小说会比莎士比亚更有价值。反之,我们也将无法正确评价李白的五言绝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二十个穿越时空的汉字序列。所以,概率与我们所说的“体验”或“客观存在”没有关系。

中国艺术家张瀚谦,搜集各朝代书法名家,包括王羲之、董其昌、苏轼等人的书法数据,输入至人工智能(AI)中,将名家的笔墨风格糅合在《封笔-墨池记》,以电子媒介重现。
的确需要指出的是,莎士比亚绝不仅仅是语词的罗列,正如乔托也绝不仅仅是图像的堆砌。是一代代的读者重读发现了他们,甚至在重读中再造了他们。基于这个潜在的事实,卡尔维诺在遗稿《新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中,对未来的文学充满了信心:
“现在是一九八五年,我们和下一轮千福年之间只剩十五年的时光。在此刻,我并不觉得新纪元的逼近会引起什么特别的情绪波动。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未来学,而是要谈文学。……我们常纳闷,文学和书籍在所谓的后工业科技时代会有什么下场——这样的关注,或许就是一个征兆,表示目前这个太平盛世即将结束。我并不太喜欢沉溺于这种揣测。我对文学的未来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唯独文学才能提供给我们的。”(伊塔洛·卡尔维诺)
他的信心来自于符号系统的机械排列之外的本体:对人脑的创造与感受能力的自信。我们充分看到,目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也仅仅只能是一个处理语义符号和图像等信息的装置。从自由意志的角度,它和艺术史上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具备真正的感受能力(那个客观存在)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创造——只是在形式上对此过程加以随机的模仿,并根据符号关联的频率进行剪枝。概言之,AI可以告诉你“夜莺的歌唱是美妙的”,但它并不能够接收“夜莺的歌唱”,也无法理解“美妙”。最终的接收者是我们,是人类在自身创造的语言和图像的海洋中穿梭,而AI只不过是我们的水下推进器。

中国艺术家陈天禅在美国纽约州的展览“Apex: Beyond the limitless”中的作品《无限极》。2019年至2021年期间,陈天禅作为北京澜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员,参与了XR技术软件的研发以及艺术市场的扩张实施。
在卡尔维诺的讲稿中,提到了五种不同的价值,分别是1)轻逸;2)速度;3)精确;4)形象鲜明;5)内容多样。由于他的突然死亡,我们至今不能确切的知道第六种“连贯”具体是怎样的。与沃尔夫林的策略不同,这些价值中的每一个都是基于本体的。他在第四章中写道:“艺术家的想象力是一个包容种种潜能的世界,这是任何艺术创作也不可能成功地阐发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适应着其他形式的秩序和混乱。在纸页上层层积累起来的词语,正像画布上的层层颜料一样,是另外一个世界,虽然也是不限定的,但是比较容易控制,规划起来较少费力。这三个世界的联系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不可思议(indecidable);或者,我想称之为无法判定(undecidable)。这是包含着其他无限的整体的相谬之处。”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新柏拉图主义般的三重结构。正如前文所述,最终表意的系统,无论是图像或是语言,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基于本体的影子。而艺术家不受限制的潜能,正如吹拂沙丘的风一样,不断变换着他固定的图像-语义之堡。紧紧贴在一起的沙粒就像我们的符号,它是恒久不变的,却又是变幻无穷的。
3
异质性:
艺术作为开放共通体的游戏
从进化的角度,人脑是为面对无限和异质性所设计的。我们的语词谈论河对岸的狮子,在洞穴中浮现它的影像,而我们的杏仁核则完美的演绎出遭遇它的恐怖。我们好奇的打量所有陌生的对象,并展开无止境的学习。艺术家是那些拥有释放无限精神力并发掘异质性的人——他们善于平衡色彩和形状,但是其目的却是不断的顺应无限的本体感受。
谁能够评价真正的杰作?作为图像、语义生产装置的AI不可能承担这样重大的职责。它们作为无本体的自动沙丘,不能够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意味着的无限的潜能。在封闭规则游戏中,例如AlphaGo在围棋中所作的那样,AI可以通过封闭规则倒推它当下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本质是运算到局终,根据最终的胜负来倒推当下一手的胜率。封闭游戏中,“获胜”可以不仰赖于真正的理解——AI只需要确保结果被程序化的执行。



艺术家刘佳玉2022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参展作品《虚极静笃》。作品以大量真实的中国地形数据为基础信息,先使用双层机器深度学习,并由人工智能生成多组不同的虚拟三维动态图形,再在虚拟的场域表皮上附着人工智能对10000张中国水墨画进行学习与训练,最终得到的结果。
但当我们进入到巴尔扎克所要描绘的客观世界中时(或更进一步进入创造力世界中),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开放游戏的共通体中。这里存在着无限多样化的价值,每一件事情的结果都是下一个事情的起因。价值从一个聚落转化到下一个聚落,就像水一样不停的流动。显然,AI无法在这样的开放规则中标记价值——这只能是一个充满精神力的人类捕捉本体的过程。
在这场注定由卓越的心灵参与的塑造游戏中,艺术家扮演着节点标记中我们称之为"主体标记"(SubjectiveAnnotation)的角色。而那些已经长存在艺术史中的伟大作品与作者,更是为数据节点赋予了不可或缺的异质性材料的典范。每一个艺术史的本体之所以成就其卓越,乃是由于其在图像和语义背后所昭示出的无限潜能。卡尔维诺以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手稿写作为例,说明了这种对无限精微的感知与想象的捕捉:
“他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捕捉这只怪兽的形象,三次尝试用一个句子来传达这个灵感给予他的一切神奇魅力……达文西追求这巨兽的幻影,几乎把它当成大自然之神力量的象征来呈现,让我们窥见他的想象力如何运作。我在这篇讲词的末尾留给各位这个意象,好让你们长存在记忆中,细细思索其清澈和神秘。”

大洪水 列奥纳多·达·芬奇 1517-1518
在这场开放游戏中,面对山中发现的海底生物化石,列奥纳多·达·芬奇运用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词汇描绘他对史前巨兽的想象。在他不断迁延的语词中,本体情境呼之欲出。在这场精神力的博弈中,艺术家无限的捕捉海水满涨的波浪中,山脉一般隐约浮现的乌黑巨兽,正是今日人类与AI的绝妙隐喻。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99艺术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