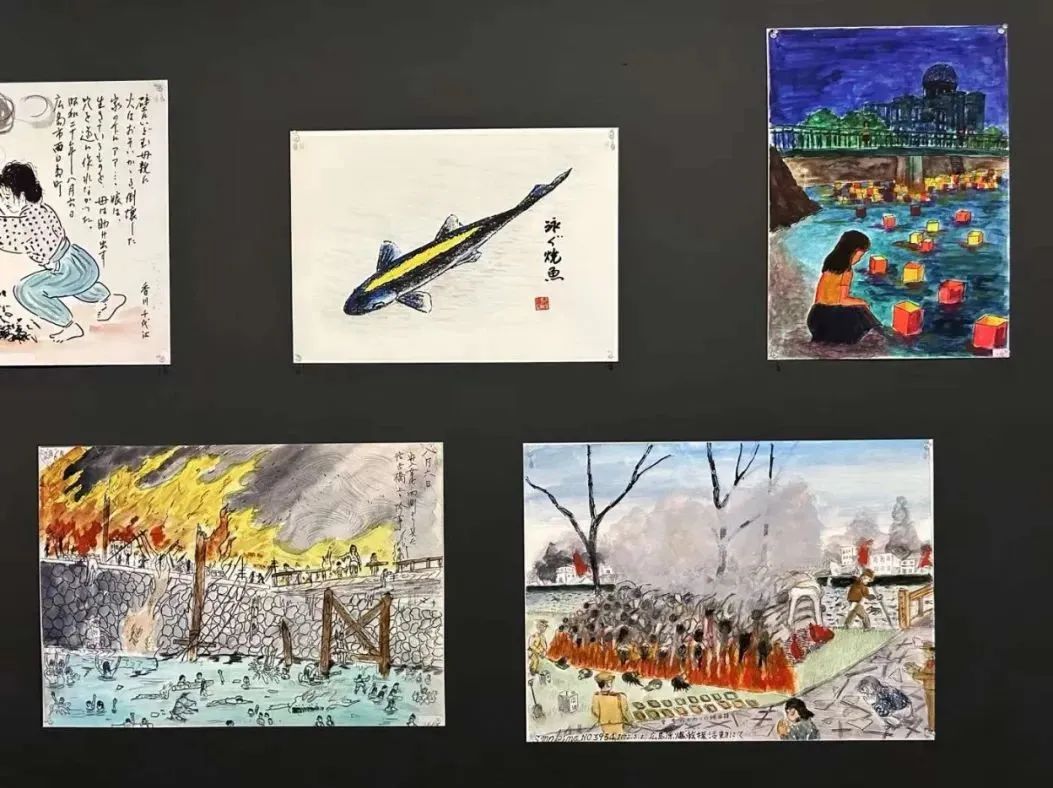- 0
- 0
- 0
分享
- 聂荣庆:一个边陲美术馆如何聚焦地方
-
2023-07-27

聂荣庆
受访:聂荣庆
采访:陈颖 钟刚
编辑:陈颖
7月22日,张晓刚最新个展“隐语之书”在昆明当代美术馆(CGK)开幕,作为张晓刚离乡40年后首度在昆明的个人展览,鞠白玉、许知远和聂荣庆三位策展人选择了以文学的角度,探索绘画作品背后艺术家的思想意向和情感关联。张晓刚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部分从未公开展示过的早期作品,以及他的日记、随笔、书信、草图等私人笔记(迹)都悉数到场。
展览里,阅读、写作和绘画的流动性,看似曲折多变,实际上都形成了殊途同归的意象,指引着发现张晓刚精神世界的路径。如同展览标题“隐语之书”所指,绘画和文字的关系若即若离,又相互交叠,展览里二者的并置,暗埋着潜在的张力,当中既有时代与个体的运行轨迹,亦讲述着一个40年来如何对家庭和故乡抱有渴望,却又保持着距离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一点,也许就从进入展场后最先看到的《我的母亲》里,一个小男孩与母亲之间脆弱而孤独的气息中隐约地传递了出来,昆明当代美术馆与策展人敏感地捕捉到了这张作品在昆明的意义。这种敏感性,同时也体现在对于展览单元的划分、对于不同时期的切割和联系,以及以不同的文学段落回应和归纳张晓刚不同时期的思想与情感之上。
文学是最能接近艺术家精神世界的一种介质,曾经在《护城河的颜色》一书里,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聂荣庆就还原了1980年代,一个物质、信息和环境都处于贫瘠和封闭边缘的时代,如何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今天的展览里,聂荣庆试图通过张晓刚的个人线索,以及被大量的历史性书信连接起来的艺术家们,验证书里提到的那一代人,是如何被经典滋养,形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为创作提供思想性价值。
展览开幕前,打边炉与聂荣庆进行了一次对话,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边陲城市里的小型美术馆,能够承办张晓刚的展览并不足以证明自身,如何在其中呈现出美术馆的气质才最为重要。他介绍,“隐语之书”的生发源自他们对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的关注,这又对应起了美术馆一系列的在地文化研究。今天,中心的光芒正在褪去,地方化成为了美术馆的“武器”,正是游离的状态,产生了不断介入现场的文化自觉性。

张晓刚《我的母亲》在“隐语之书”展览现场 ©️ARTDBL
不渝的理想
ARTDBL:作为张晓刚40年来在家乡昆明的首次个展,展览“隐语之书”为何选择以文学的角度切入?张晓刚的创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想的?
聂荣庆:在这个展览以前,鞠白玉、许知远和我三个人正在围绕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关系展开一个系列研究,希望可以来策划一个“西南联大与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主题的展览。抗战时期南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对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奠定性的作用,而当时同期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影响也是极为巨大的。当时西南联大和国立艺专同在昆明,不同学界的好友多有往来,师生之间互动频繁,一流的学术与艺术理念也因此传播到了云南,为云南留下的艺术的种子影响至今。这个话题要深入进去,无疑是一个跨学科的大工程,我们一直在探讨从哪些切入点可以介入展览,相关想法及线索的梳理工作,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之所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提到西南联大的研究,是因为张晓刚与之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我们三位策展人的工作都与文字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展览命名为“隐语之书”,就是要从我们的角度探寻一条线索:艺术家的阅读史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张晓刚作为一个既与昆明的人文历史有关联,又在这里成长,汲取了养分的艺术家,在这里探寻他的原初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中可以探讨的话题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这个展览有过很多个方案,是一个不断被推翻重建的过程。我们甚至把张晓刚在1980年代读过的老版书全带到了昆明,研究这些书对他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他的创作和思想由此产生过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研究的是张晓刚的个人精神史,这才是指导他各个时期创作的基础。
当然,这种精神养分并不具体指向某一本书,并不是因为读了哪一本书就画出了“大家庭”。所以,我们将文学与绘画作品结合,但又竭力避免将阅读和创作直接对应起来,呈现出看图说话的指向性。往深一层,我们找寻的关系,是1980年代整个中国的思想运动过程中,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学术风气进入到了艺术创作语境当中,激发了那一代艺术家学习热情的线索,研究文学如何影响过艺术家的创作。
ARTDBL: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研究是美术馆一个长期研究项目和线索,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张晓刚的创作线索对项目而言具有启动性意义,张晓刚和西南联大之间直接的关系是怎样的?
聂荣庆:我们当初和张晓刚聊到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曾经一起回顾了西南联大和他的父辈对他产生的一种直接影响。张晓刚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当年从广东东莞去了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了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他的爸爸在西南联大加入了进步组织,是“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去参加边纵游击队。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长大的张晓刚,与父亲有着一样的读书习惯,哪怕是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他也千方百计找各种图书来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在张晓刚的成长过程中,不像现在的艺术家那么专注于艺术的形式,思想与文学在这当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他的书信集《失忆与记忆》里就可以看到,写作在他的创作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这次把他压箱底的文章和手稿都拿了出来,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找寻阅读和创作的关系,也能看到张晓刚从学生时期开始,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其中的联系。
张晓刚属于少年得志的艺术家,23岁就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作品,那会儿他的成功与商业、事业并没有任何关系,工作依然难找。这个展览除了探寻文学与绘画创作的关系外,也希望让观众能清晰地看到张晓刚从学生时期到今天的作品面貌及创作思考过程,让人们能看到另外一个不只是画“大家庭”的张晓刚。

“隐语之书”展览现场 ©️ARTDBL
ARTDBL:张晓刚和昆明的关系千丝万缕,为何离乡四十年后才首度在昆明做个展?展览背后的渊源是什么?为何发生在昆明当代美术馆?
聂荣庆:虽然张晓刚一直和云南有关系,但他在昆明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毕业后,他曾在昆明待了四年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四川美院教书,结婚后去了成都,又从成都去了北京,所以很难界定他的地方性。昆明作为故乡,他每年都来来往往,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但在昆明的时间大多也不是工作的状态。但有意思的是,他每一个时期转型最成功的作品,创作风格都是在昆明形成。所以在自己的故乡,创作的“福地”,他必须要向故乡的亲人朋友作一个汇报,给逝去的父母一个交待。
我和张晓刚有将近40年的友谊,在六年以前,昆明当代美术馆成立的伊始,为张晓刚做一个重要的展览就成为了我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的不渝理想,今天终于美梦成真。
我们三个都不是在当代艺术圈里能和张晓刚这个名字对应的策展人,这恰恰能让我感到兴奋。美术馆邀请某个成熟的策展人,考虑哪些策展人配得上哪些艺术家,无非是中规中矩的搭配,这反倒不是美术馆应有的态度。深层次的专业和学术研究是需要的,对于美术馆而言,有经验的策展人固然是好的,不仅是学术上,在预算和呈现上能做到比较细节把控。但在我看来,美术馆依然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就像巴黎毕加索美术馆正在用时装设计师保罗·史密斯的视角来做毕加索的展览,为毕加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呈现方式,这就比较有意思。
我们这个美术馆的好处在于,这是一个“小馆”,不用担负那么大的责任,高举学术的大旗。我们不用去考虑价值的输出和知识的生产,只是需要注意自己的发展方向,对每一个展览作出自己独立的阐释。

张晓刚自画像
资本与理想的对赌
ARTDBL:在1980年代,作家和艺术家都玩在一起,后来文学和艺术越来越专业化,形成了平行的关系,虽然也有一直持续在做文学活动的美术馆,但更多的是美术馆的专业性把文学挡在了门外。你怎么考虑美术馆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聂荣庆:实际上,生活并不能离开文学,文学对每个人的影响是持续一生的,哪怕在今天这种信息泛滥、阅读崩溃的互联网商业社会,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影视,其实也是在谈论背后的文学。在这个展览里,正巧碰到了我们几个平常一直保持着文字写作的人,就更有兴趣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谈文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文学对于介入社会现场并没有那么活跃,反而是美术馆不断地在调动地方资源,然后去输出和生产一种现场,同时也去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作家的静态输出和社会还是有距离的。现在很多作家和文学机构都来靠近当代艺术,以艺术的方式和城市进行合作和连接,这当中,调动的方法、生产的现场可以多样而丰富,建立的影响力可以更深远,也更有效,我们可以看到,艺术或者美术馆在这当中做的工作其实更加灵活。

“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 ©️CGK
ARTDBL:昆明当代美术馆为什么选址于繁华的商业广场?
聂荣庆:在中国,很多美术馆都被建在城市的开发区里,这些新的区域,一般都地处偏僻,配合着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进程,交通、生活配套和人流都成问题,于是每一次开幕,美术馆都需要花力气组织人们“跋山涉水”去到现场,然而开幕式结束后,也就没有太多的观众再进入到美术馆当中。这是地产项目需要的美术馆,并非城市需要的美术馆。在我看来,对一个城市的当代美术馆而言,公众性是十分重要的。运营昆明当代美术馆,我希望除了专业观众以外,最重要的指标是公众也可以容易地走进其中。
美术馆的建成是在公园1903这个商业区开放三年以后,商业项目需要艺术和文化来提升调性,美术馆也需要人间烟火和商业支撑来支持运营,在一种共赢的合作状态下,几年下来相得益彰。虽然处于商业区,但靠美术馆赚钱肯定还是不能指望的。每年美术馆的预算和展览选题的自由,就像是资本和理想情怀的一种对赌。在边陲云南,每年能有固定的经费可以来维持美术馆,让学术委员会独立地决策展览,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在商业区里,美术馆的面积自然是受限的,但其实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巨型美术馆。我们除了看中了这个地方的人间烟火,重要的是,美术馆现在的体量正好是我们能够游刃有余的范围。资本和体量与美术馆自身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权衡利弊的,我还是更希望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模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尽量减少遗憾。
ARTDBL:你如何看待昆明当代作为一个机构的生命力?
聂荣庆:在中国很难考虑长远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能有一种模式,来充分发掘云南独特的丰富性,我考虑过未来能以CGK这个馆为中心,在云南不同的地区形成一个小的美术馆集群,比如沙溪、红河等等地方,能有一个空间开展不同的在地性研究,在昆明有昆明的方式,在沙溪有沙溪的模式,这肯定得有研究,但既然先锋书店都能在沙溪做成旗下卖书卖得最好的地方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就肯定有可以做美术馆的土壤。对于馆群而言,只要有合适的空间和建筑,以及持续的支持资金,就能深入进去。

“隐语之书”展览现场 ©️CGK
自己长出来的蘑菇
ARTDBL:你的美术馆经验来自哪里?
聂荣庆:我这辈子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和艺术相关,我和当代艺术的关系一直保持着游离状态,从未离开艺术圈。平常我除了美术馆运营管理的理论学习外,在不同城市不同的艺术机构、博物馆、博览会里的学习对我也尤其重要。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到达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美术馆、研究展览。疫情之前,我在欧洲旅行时,经常一天下来要步行差不多15公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美术馆里,这种经验是直接的,当然还有与同行朋友的相互交流。
有一年在欧洲,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逛进了柏林汉堡火车站现当代美术馆,突然看到了“黑山学院:一个跨界实验,1933-1957年”这个展览,那是一种让人震惊的感觉,虽然在语言上有障碍,但视觉和展览呈现能直击你的心灵,用心做的展览就能让人记忆深刻,但抓住我的不仅仅因为展览呈现本身。我在那个展览以后,重新研究了黑山学院那段历史,依然心潮澎湃,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黑山学院特别注重在地性体验,云南丰富的在地性面貌,包括东南亚、南方当下很多艺术实践和创作思想,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打开和结合。

“隐语之书”展览现场 ©️CGK
ARTDBL:美术馆工作是你现在的职业重心吗?
聂荣庆:我从青年到中年,都是标准的“斜杆青年”到了“斜杠中年”,没有所谓的“主业”,都是副业。对于自己热爱的东西,无利也要做,像在昆明运营美术馆这种事物,很多艺术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我不做谁来做?昆明当代做了六年,它在我心中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个美术馆,也是这个城市应该有的一个美术馆,所幸这个城市还有一间当代美术馆,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当代艺术与昆明还有什么关系。
ARTDBL:你现在怎么看昆明的艺术生态?
聂荣庆:大体上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毕竟时代都在进步。我认为云南最大的问题,还是艺术教育的结构问题,虽然现在学校很多,学生也很多,但不像从前,现在的学生似乎只是需要一张文凭。每年都有一些人留下来做艺术,也有很多人离开或者转行,艺术成为了一段学历而已,当然,这个现象在中国都是普遍的。只是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与云南的当代艺术发展传统有种青黄不接的感觉,相对于前辈,新一代的云南艺术家稍微趋于保守。
但有意思的地方是,现在很多孩子出去读书,在国外的艺术大学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回到云南来,觉得这个地方有他们想做的事情,比如程新皓,在北大读完化学博士,又回到云南坚持做与在地性有关的作品。一些在外地的艺术家,也会选择来到云南做他们的作品,比如像童文敏,这种风气慢慢有了一种回归的趋势。
云南天高空气稀薄,人脑袋比较漂浮。这个地方的土地最适合种的不是庄稼,而是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蘑菇自己都会长出来,人在这里想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都是形而上的,更容易产生艺术家。

“谱系+ ——1978 年以来的云南版画”展览现场 ©️CGK
ARTDBL:你在这个地方成长,经历了1980年代的乌托邦,今天你在这里做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乌托邦的概念了,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语境。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聂荣庆:这种变化其实不仅发生在云南。我记得当时《护城河的颜色》成书了以后,黄专老师在病床上读完,给我写了一条很长的微信,他说读完以后非常激动,希望我继续往下写后面的20年。他说他很欣喜地看到我写的1980年代的一个乌托邦时代,那个时候所有的艺术家都朝向心中的理想。1990年代有了各种展览的机会,在经济发展的状况下,艺术圈产生了分化,成为了“异托邦”,2000年以后,随着艺术市场、代理机制的起来,中国的艺术真正地进入了市场以后,转向了“恶托邦”时代。
实际上,区域化在1980年代并不明显,张晓刚那四年在云南的时候,信息反倒不闭塞,每天南来北往的各种人,一会北京来一会广州来,在昆明过一站住一晚上又走了,带来了各种信息和新的鲜活的思想,而他回到四川美院教书以后,学校里面就像马尔克斯描写的马贡多一样,每天都是几个熟人在一起,反倒是封闭,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其实整个1980年代,虽然是乌托邦的时代,但重要的是来往的这些人思想都特别鲜活,在昆明这个地方有很多交流,有些人走了,又来新的,有非常好的信息和思想交流的场景。
其实在八五新潮时期,相比北方艺术群体的理智,西南的艺术家更趋向于一种生命的本能,想到哪就做到哪。在我看来,云南艺术家对于中心名利的追求并没有那么明显,张晓刚很早就去了北京,并不是因为市场,阿昌也是因为云南实在没有行为艺术的土壤,连做展览的地方都没有,才去了北京。像毛旭辉,坚持呆在这个地方那么多年,甚至到现在几乎都不参加任何展览开幕了,也不妨碍他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存在。
从整体上,现在要从云南发出声音似乎比较难,但可能他们也不太热衷于要往中心去发声。那种游离的状态,可能不需要去占领什么地方,而从中产生了一种自觉。

美术馆与边境
ARTDBL:有本书叫《逃避统治的艺术》,谈到在云南或金三角的逃离和避世,你在这里生活那么多年,你怎么看待这里的“南方”?在这里如何连接东南亚?
聂荣庆:中国的南北差异还是蛮大的,就像南欧和北欧,人的状况、生活的方式和产生的艺术都不一样,只是中国文化对大一统的强调,好像形成了一些标准的唯一性。其实,今天的时代是允许非标准化和保留各自特点的。我也欣喜地看见像“榴莲·榴莲”这样的一些展览,把南方的概念做出来。其实早几年开始,我们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四年前我还甚至想邀请阿彼察邦这样的一些艺术家到这里来,参加关于南方和东南亚的展览,只是被疫情耽误了国际交流。
在历史上,云南可以说是一个避世之地,经济不好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人们都往这里跑,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性里,我们和东南亚国家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就带出了另外一种国际化概念,那是和北上广不一样的国际化。
事实上,云南人本身的生活就很避世,一般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太像云南人,总是往外跑,去关心外面的事情,总想把外面好的东西带过来,就像山里卖土货的老板一样,家里面有点什么山货,就想办法把它售卖出去,外面有什么好东西就带回来。

ARTDBL:边境叙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广阔空间和运动的状态能给主流的中心或历史叙事提供质疑,在云南,主流语境以外,提供怎样有趣的经验?
聂荣庆:疫情之前,我每年会到在清迈住一段时间,这里的边境题材是一个悠久的历史问题,当年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缅甸、泰国边境驻扎下来,一代一代繁衍了下来,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社会。他们之中的一个后代赵德胤,早年有一个电影叫《再见瓦城》拍得很好,拍出了那种青春残酷。它真正代表了地方社会学的状态,大家看阿彼察邦的作品永远都鬼里鬼气的,当你到清迈一驻留,马上就知道了,那个城市就是这种感觉,那就是阿彼察邦的南方。我们也希望未来在金三角、缅甸或者泰国有驻留计划,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一些艺术家去驻留。如果我们的小集群成立,驻留是可以实现的。
非静止的叙事和意识形态在边境更能体现出来,在中国,不同的边境城市,美术馆呈现出来的气质完全不一样,在云南,东南亚的感觉更为强烈,在丹东更能看到中朝边境的特殊性,银川体现的则是一个天地之间的西域,我觉得这就对了,每个美术馆其实都应该有它的特点。
中心的光芒慢慢地在衰减,每个地方可以形成自己的中心,可以独立地去和全球化网络来去联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隐语之书”展览现场 ©️CGK
ARTDBL:在不同的城市做展览有不同的节奏,深圳追求效率,北京追求的则是专业生产,在昆明,似乎没有办法让大家快起来,去经营有效率的生产,外来的策展人也要去适应这种地方节奏。这种节奏和美术馆,如何在地方形成关系?
聂荣庆:昆明的城市气质和别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慢的节奏可能来自一种生活在高原的“缺氧状态”,高原的空气比平原稀薄,人在这里都有点飘飘忽忽的。我们的员工忠诚度和专业性都很好,但工作节奏真的不比北上广深,有时候我也很着急,但我还是坚持用他们。在我看来,包括我们的外籍员工,他们对于艺术的热爱是根深蒂固的,因为热爱才会来做这份工作,而不是因为其他。所以,哪怕有节奏问题,我们依然坚持做那么多大型展览。慢一点没有问题,只要态度是正确的,工作是专业的,水准是合格的,我们就能坚持下去。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打边炉ARTDBL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