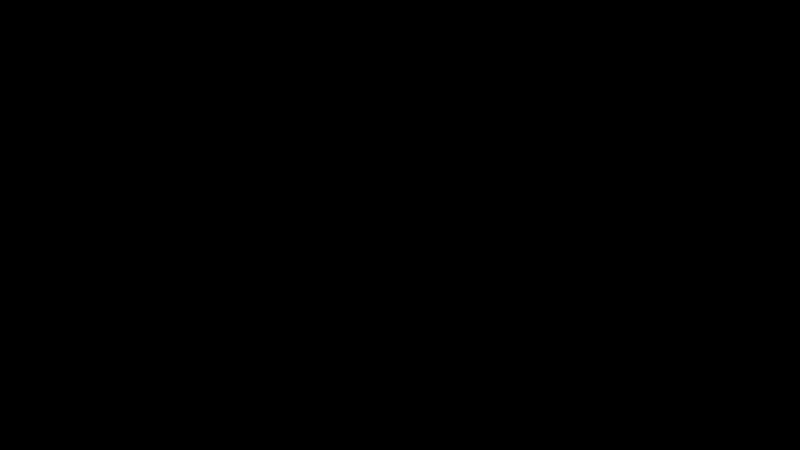第二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评审现场 ©️成都当代影像馆
成都当代影像馆举办的第二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于2023年4月28日落幕,经过推选委员推选,蔡东东、陈维、陶辉与杨福东四位艺术家获得“杰出摄影艺术家”奖项。经过五位终审评委的评议与票选,陈维最终摘得“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获得现金奖励30万元人民币。
成都当代影像馆邀请《打边炉》作为唯一在场媒体,见证了评审的现场,我们得以切身观察这个摄影艺术奖诞生的全部过程。以下是《打边炉》对第二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评审现场实录,按照评审当日的线性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奖项背景及规则宣读、艺术家陈述以及评委评议。
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组委会秘书长王达军(右) ©️成都当代影像馆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的大奖评审现场。由于此前疫情,第一轮评审是在线上进行,经过这一轮评审,有四位摄影艺术家获得“杰出摄影艺术家”奖项,以姓氏拼音为序,他们是:蔡东东、陈维、陶辉、杨福东。本次终审将在四位艺术家中,评选出一位获得“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的艺术家。首先,我将简单介绍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的历史与奖项定位,接着将介绍大奖评审现场的评审议程。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由成都当代影像馆为鼓励创作者设立,该奖项表彰的对象为30岁至60岁,在中国当下影像文化的语境下,正在持续创作的影像艺术工作者。2019年,第一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评出了十位“杰出摄影艺术家”奖项获得者,其中张克纯获得“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在第一届的基础上,第二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再次启动,评选过程经历疫情,有很多障碍、很多困难,经历一年多的努力,整体工作已经达到了尾声。评委以姓氏拼音为序,是:中国摄影评论家鲍昆、加拿大多伦多美术馆馆长凯瑟琳·巴特尔斯、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家栗宪庭、中国独立策展人及当代艺术评论家冯博一、日本森美术馆馆长片冈真实。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的组委会成员是:总策划钟维兴、艺术总监王庆松,我是秘书长王达军。
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金熊猫摄影艺术奖总策划钟维兴 ©️成都当代影像馆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艺术总监王庆松 ©️成都当代影像馆由于疫情以及其他因素,两位海外评审未能到终审现场,根据要求,二位评审已提前向组委会提交了他们的评选结果,这两份结果也将在最终统计中,纳入奖项的评选。下面我将叙述“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评审的评选机制。根据组委会规则,艺术家必须到现场与评委讲解自己的作品,并到场出席领奖环节,如若不能,则视为自动弃权。杨福东先生已提前与我方沟通并确认,他因特殊情况无法到场,故放弃参与本次评选。三位现场评委将基于蔡东东、陈维和陶辉三位摄影艺术家的个人艺术成就、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在展览现场的陈述等,以打分的形式(十分制),对三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进行综合评审。根据最终的得分,得分最高的艺术家将获得大奖。评委在评选时,除了要看参评人的送选作品,更需注意参评人整体的艺术成就与道德品行方面是否有严重污点。第一,评委有权利和义务,对参评人及作品发表自己真实的意见,或保留自己的看法。第二,评委不应受任何干预,公平、公正地对参评人及作品进行投票。第四,评委在评选全过程不得与参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沟通任何关于评奖的相关事项,不得接受参评人及相关人员任何馈赠、宴请或请托。第五,评委有保密义务,未经组委会或评委会的许可,不得对外传播个人评选的结果、评委的意见、以及参评人得票情况等相关评选信息。下面我们将一同移至作品展览现场,由三位摄影艺术家为评委讲解自己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将有十五分钟的交流时间。
蔡东东:过去七年我完成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照片游戏”,本次展厅中有二十余件作品来自这个项目;另一个是“生活史”,它与“照片游戏”相伴而生,以一本书的形式呈现。七年前,我感到在摄影上很难实现突破,于是有两到三年的时间没有从事摄影。在一次清理废片的过程中,我无意中撕破了一张照片,发现撕开的痕迹恰好破坏了照片内部稳定的结构,这个行动,让照片复活了。桑塔格曾说过:“照片是对死亡的一种提示”。后来,我采用了许多针对破坏照片并重构照片的方法,慢慢养成了一种工作方法,即:等待与发现。我先将那些我预感可以成为作品的底片洗出来贴在墙上,然后就是等待,等待照片给我启发,发现新的结构,这种结构应该是一种自洽的关系,而不是我强加给照片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照片自身有一种意识形态,而我在做作品的过程,便是试图重塑我与照片之间一种新的关系。陈维:这里有两个在创作时间线上并行的项目,一个是关于跳舞与聚集的“俱乐部”系列,还有一个是“新城”。后者这个有关中国城市化的项目其实是从2013年开始,要在2018年结束的,但过程中经历了清退,又经历了疫情,城市的概念在所有人的理解中一直在改变。现在许多关于城市的讨论,我觉得都跟我自身相关。1990年代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而我在那时正慢慢进入青春期。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地方,到更大的城市读高中,又到了更大的城市继续求学,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对“更大的城市面貌”的想象。在过去七年,我的工作室搬了五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是,艺术家是以游牧的状态来做作品的,同时我也开始反思:这个一直让我搬、让我游走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机制可以产生那么多临时建筑,为什么有那么多拆了一半之后、第二年这一半还在的建筑?以及,我们是如何与这些景象平安无事地相处,直至无感的?我们总在讨论中国的城市速度太快,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记录这些的文件夹,去打开的时候是空的,很多地方也是空的,北京郊区的人可以一夜之间全部赶走……我时常感到这些东西是不被记录的,这些就是作品创作的大概背景。我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先从网络收集资料,能到现场会尽量走到现场,然后,我的拍摄全部都在工作室里完成,在工作室里,我会重新去做建筑,复写现实,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过程,像写作一样,这是编辑的过程。在创作中,我从不把自己当作摄影师,而是一个写作的人。第一件作品,《德黑兰的黄昏》,想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讲女性对自己的诉求。梅艳芳在她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上跟歌迷说,自己人生中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结婚,那时她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可能还有一个月的生命。2013年在伊朗做驻地的时候,我让一位伊朗女生穿着婚纱,扮演歌手坐在车里。伊朗是不允许女性在公开场合表演的,也就没有女歌手这个职业,作品谈的就是香港和伊朗这两种完全不同社会状态下的两位女性,对于讲述的诉求。第二件是《类似装扮》项目的剧照,这是一个在抖音上的五集短剧,每集一分钟多,讲的是面对屏幕表演的创作者,由于不停地拍摄自己,最终迷失自己、不知道表演对象是谁的状态。由于现在大家的观看习惯,我希望短剧的视频是在手机上播放,而非直接在美术馆的空间里进行展示。在网上,每一集视频的播放量都有七到八万,这些人或许并没有艺术背景,但是这样的流量比美术馆的人流量好像还要大一些。我希望观众不需要通过画廊和美术馆就能看东西,我也想看到,当没有艺术背景的人看到艺术创作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第三件作品,《跳动的原子》,是想讨论现在的社交以及观看方式的。很多人以为是我在抖音下载的视频,但实际上是用抖音的样式拍摄,然后再将许多短的视频拼凑在一起的,它们形成一个更有叙事性的作品。很多人批评现在的短视频和社交软件让社会变得“原子化”了,我们面对屏幕看到很热闹的东西,实际上每个人都越来越孤独。《全息建筑》是采用了197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家的技术呈现的,和摄影不同,全息技术利用了透镜,摄影记录的是光的深浅,但是这个技术记录所有光的信息。我选用的是房地产楼盘售楼后废弃的沙盘模型。
摄影评论家鲍昆 ©️成都当代影像馆
栗宪庭:我觉得这次几位艺术家进入奖项,最重要的是关乎他们的工作方法,每个人都非常特别,有自己的工作方法。我最有感触的是陈维。我刚才对冯博一说了一句话:搜尽奇峰打草稿。陈维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传统摄影的工作方式,拿着相机在拍,而是在浏览。陈维的一句话对我很触动,他说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正是他的青春期。而城市化正是中国的青春期。在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有文化价值在背后支撑,我们的城市化,是在许多利益、金钱、和权力等基础上突然开始的,所以,你找不到它背后的规则。陈维所看到的场景并不来自现场拍摄,而是他根据记忆中的深刻印象,在工作室重新制作出来的。在制作的过程中,陈维自己的感觉也在强化。你能看到他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烦躁、焦虑、困惑和痛苦。冯博一:陈维是80后做得比较好的影像艺术家,有想法,善于思考。我对于他这次的作品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画面上并不能特别明显地看出那些场景都是他自己搭建的。在我们了解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工作室里不断搭建、拍照的情况下,这个方法本身是OK的,但是这个方法在画面上的呈现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拍城市化的、拍雾霾、拍疫情的非常多,我觉得艺术家拍太常见的东西,好像有些不够。而蔡东东相对来说就比较线性,看他的作品,反而一下子就能够知道他的想法和他的针对性。鲍昆:我和老栗一样,对陈维印象很深。我先是在网络上看作品的,到现场之后跟原来的阅读有巨大的反差。陈维的作品很缜密也很深,他的处理方式有很多隐喻,诉说一种未来世界的真实。他的工作方式非常有意思,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人们对叙事的基本准则已经变了,我们对历史阐述的方式也变了,不再是单纯用摄影“咔嚓”去记录。栗老师说得特别精彩,他注意到陈维说青春期的时候,栗老师说城市也是青春。现在来看,整个中国在30年来突然进入了短暂生命期,迅速辉煌,迅速衰老,迅速消散。还有,我知道陈维的劳动量有多大,当然陶辉工作量也很大,但是他们俩的方式不一样,比如陈维的第一幅作品,《铁皮》那个折叠的铁皮,看上去就像高楼大厦,又把一些梦影投了进去,做得很复杂。做摄影的人,内心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就是我必须要咔嚓真实的东西,可是有时候你无法到达现场,历史也已经消失,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鲍昆:没错,关键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栗宪庭:蔡东东呢,是根据每一张照片,设置一个现场。比如说“喜儿”,是绳子、帘子等其他很多装置的结合。帘子那件作品收集的是证件照,我想,如果不是证件照,会对人的冲击更大,因为证件照是相对格式化和严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蔡东东的作品是很幽默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消解。文革的时候,我在一个省重点中学读高中,那时候有一多半的老师以前在大学教书,被当作右派贬到中学了,文革刚开始的那个夏天,我们高中的校友回到学校来造反,把一个历史老师的照片抄家,都是在1930年代时期的上海拍的,那一堆照片对我的冲击很大。我是第一次看到1930年代的照片,因为我成长的年代,能看到的服装,非常单调,颜色也以蓝灰白为主,没有想到三十年代上海那么时髦、开放,包括照片中人的气质,都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所以我觉得证件照削弱了时代的特征。鲍昆:蔡东东没有注意到栗老师提到的,用证件照的方式体现民国、红色以及改革开放这三个时代,实际上是削弱了他的观念的。用旧照片演绎和重新叙述,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做得很多,但苏文反而更有冲击力,而蔡东东更多是形式上的思考,像是严肃过头了。比如拉一根线,这个东西是好玩,但是,像个游戏,冲淡了背后严肃的思考以及照片拼合后的透视关系。冯博一:像栗老师说的,的确是有消解,但是也有一个转换的创作,老照片是一个层面,转换、做装置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栗老师说的“幽默”。我觉得蔡东东对于沉重的、带有痛苦的历史,以一种来自现在的幽默态度进行了转换。我觉得蔡东东的作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他利用的基本都是老照片,利用老照片本身带有的记忆资源,作为他这一系列作品的起点,二是他并非直接取用老照片或者对着老照片再照,而是进行了一个转换,按栗老师刚刚说的,像摄影装置,或者说得比较“装”一点,叫重置记忆。摄影装置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蔡东东说的叫“游戏”,实际上他对于每一幅选定的作品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其实摄影和其他所谓艺术创作,都是转换的过程。而且蔡东东是有针对性地挑选这些老照片的,它们跟时代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这样导致了在观看方式上的一个改变,这是挺动脑筋的,观看方式变得带有更多蔡东东个人的创造性在里面。我觉得这与其是蔡东东个人对记忆的艺术转换,不如说是集体的共同记忆,这个记忆是社会、是时代的大手笔,我们都裹在其中,在劫难逃。所以,在观看方式上,已经不是简单的看和被看的传统方式,因为蔡东东对于照片的改变,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创造了记忆。记忆,在感性层次或许是一个故事的复现,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记忆是有创造性的,往事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蔡东东以影像的方式,实现了记忆的在地再创作。栗宪庭:陶辉的东西也很好,它更接近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看短视频、看很多照片。陶辉的每一个照片都让你感到“莫名其妙”,像是从一个故事当中抽出来的一个瞬间,当陶辉不把完整的视频在现场播放,而且每一个瞬间都有戏剧性的时候,我想每一个观众都会根据这个瞬间,自己设计一个剧情。鲍昆:我认为陶辉呈现了媒介与现实之间错乱的关系,如同说梦话以及神经质般错乱的现实,这种呈现其实很深远。陈维和陶辉的作品都带有一种哲学意味的深刻思考。他们两位艺术家都是以自己的编码方式产生叙事,给读者和观众在阅读展览时所产生的思考提供了很多线索。冯博一:看陶辉在伊朗驻地做的作品,马上就让我想到李巨川在2000年做的《北京城墙2000》,当时以影像和行为的形式完成的“梁思成纪念馆”,也是雇了一辆出租车,记录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在车上一边聊天、一边嗑瓜子,沿着北京二环转了一圈,陶辉的这个作品让我想起李巨川的那个影像。我觉得这种方式在2000年后使用得比较多,而我比较关注的是,陶辉作为接近90后这一代,对于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对此的艺术表达,所以这一件还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简单,或者说在视觉呈现上和他所要表达的,有一点错位、有一点距离。陶辉其他的作品,我很好奇,跟现在流行的抖音到底有什么区别?艺术家创造性到底体现在哪儿呢?鲍昆:在画面上是没有区别,但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文本能够产生新的意义,需要很多后续的条件,比如早期把地砖放到美术馆里这种典型案例。当现在我们把抖音这样你平时在家中上厕所的时候看的东西,放到艺术场馆里,并且用灯光、用艺术范式去对其进行处理的时候,它的意义也就转变了,出现了另外的意义。冯博一:那我还是要追问,意义是什么?场景和场域是换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层面。如果仅仅是简单地说把抖音的截屏视频转换到成都当代影像馆,或者模仿抖音的拍摄感觉,而这种视觉呈现和宽泛抖音视频的概念没有区别,抖音本身也已经有它自身的意义了,那么,一个艺术家何为?鲍昆:抖音是非常碎片化的现象,但当陶辉把抖音处理成为一个艺术文本,并集中地放在一个展览空间中,我理解他是把现实、媒介与生活,以及真实、虚幻与梦想进行了重构。冯博一:但是,我对当代艺术一直有一个看法,艺术家还是依靠视觉艺术的方式来呈现,艺术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如果艺术家的视觉语言转换得不好,或者作品高度依赖文字的上下文补充,我认为这并不是很好的视觉艺术家的方式。我注重的是最终在展厅中,作品的呈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不管是装置作品还是影像作品,艺术家由作品呈现所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不应该出现模糊或语义不详,因为再怎么说,作品最后还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展示,不论是给专业观众看,还是一般的观众,这个方面都需要考虑。
栗宪庭:疫情期间我参加过好多奖项,这个奖项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规模比较小,而且获选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传统摄影之上开辟了新的工作方法。我离开艺术界很多年了,每次来做评委,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在做什么,这对我也是个刺激。我看到今天的这几位艺术家,通过摄影与影像媒介体现了各自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比如蔡东东使用老照片,通过一种类似摄影装置的手法,表达了一种幽默的态度,这种处理方式表示了一种与时代也好、与环境也好、与老照片也好,之间的一个有距离的观看。我的最高分是给了陈维,不光是因为他说“自己的青春期是中国的城市化”那一句,还因为我看到他的第一个作品,画面中很廉价的墙体拆掉之后,背后金属板反射出来的五光十色,同时,这个背景是一个未来城市,在模模糊糊的雾霾天气中,五光十色包含着城市的拆迁,而未来却是像雾霾一样茫然的。中国的青春期可以说是在1990年代,那也是中国疯狂的城市化进程,那个阶段有许多社会问题,青春期也是这样的,有很多焦虑,而陈维从外界城市化的过程中如“搜尽奇峰打草稿”一般采集,把他的情感以及他曾经看到过的现实景观,真实地在工作室中搭建出来,这些东西就像一个青春痘,它的出现与发作,都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人内心的感觉,所以我给陈维最高的分数。陶辉的作品表达了大家目前共同的经历,不管是十几岁的孩子,还是八十多的老人,大家都在看短视频、都在玩手机,陶辉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索引,以短视频这个媒介结合摄影和影像。陶辉有许多固定、静止的照片,但这些照片的静止并不像传统摄影中那些“经典的瞬间”,也就是一些完整的、说明很多问题的瞬间,他所有的静止照片都不能说明问题,恰恰是因此提供了一些陌生感、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与环境关系,每一个观者可能都会对陶辉照片中的人物产生不同的故事编造,陶辉也是通过照片,给了所有观众一个悬念:你,怎么编造你的故事?
组委会:栗宪庭,让-吕克·蒙特罗索,王达军 ,王庆松,钟维兴推选委员:董冰峰,李峰,李振华,黄笃,尤洋,欧宁,王春辰,张然,朱炯
大奖评委:鲍昆,凯瑟琳·巴特尔斯(Kathleen S. Bartels),冯博一,栗宪庭,片冈真实(Mami Kataoka)
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artdbl2017,电话:0755-86549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