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 0
- 0
分享
- 杜静怡:论想象剧场的构成
-
原创 2023-04-04

内容摘要|Abstract
本文探讨了当代戏剧的一种新趋势——“无演员”戏剧和声音剧场。以实验性戏剧《语音百科全书—第四篇》(Encyclopédie de la parole suite 4)为例,本文回答了“无演员”的幽灵剧场何以通过缺席来唤起存在,又如何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的混合性媒介构建虚拟的“身体”的问题。当传统演员消失,多种媒介在舞台上发挥着共存和竞争的关系,一个碎片化的故事将以“蒙太奇”的方式被拼贴起来,那些消失的声音即将复活,人类的话语的历史也将被重塑。
关键词
“无演员”戏剧 ;声音剧场 ;存在与缺席
“Actorless”Theatre ; Sound Theatre ; Presence and Absence
幽灵既不死也不活,既不存在也不缺席。[1] (142)
—— 丹尼尔-布格诺
(Daniel Bougnoux)
《语音百科全书—第四篇》(Encyclopédie de la parole suite 4)是乔里斯-拉科斯特 (Joris Lacoste) 和音乐家皮埃尔-伊夫-马塞 (Pierre-Yves Macé),塞巴斯蒂安-鲁克斯 (Sébastien Roux) 一同合作完成的该系列的第四部作品。从2007年9月以来,艺术家们一直在收集各种录音以建构一个国际化的语料库,并通过再生产 (reproduction) 重构了一个碎片化的“故事”。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过去的声音化做一个个幽灵,以文字-图像-声音的集合体形式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身体”,它们将以缺席的方式被重新召唤到舞台上。当传统的演员的身体消失,传统的线性故事被抛弃,戏剧应该如何叙事,又如何保持其生命力?这部作品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艺术家们通过蒙太奇的手法拼贴了不同的叙事媒介,让消失的声音复活,让不存在的人在观者的想象中存在,或者更准确来说生产了一种“存在感”,并且重塑了一场关于人类话语的历史,制造了一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遇。那么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该戏剧中不同感知媒介的分析来回答该“幽灵”戏剧是如何构成一个想象剧场的问题。
一、文字的想象
虽然该剧中并没有传统的戏剧故事,然而并不意味着它取消了文本的能量,该剧中的文字媒介是一种综合性的媒介,它同时是文字的,图像的,声音的。单从语言的层面而言,该剧收集和选择了不同来源和不同场景的声音,它们源于戏剧,演讲,新闻会议,YouTube视频,电影,电话录音中的语音截取,或者直接来源于城市中的声音的记录,它们似乎是散乱的,是无法被链接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性,即它们都属于人类的话语,它是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是构建人类主体性的工具。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话语与权力有关,一方面它被社会文化所限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个人的表述系统。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语言和话语来塑造自身和描述世界的,语言是我们思考和交流的方式,而话语则是我们对语言的个性化的使用。又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当出现话语时,必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行为主体。而我们就是通过想象一个“空的主体”的行动和其行动的环境来理解这出戏剧的,然而有趣的是当观者观看并聆听到不同人的话语图像时,观者对话语主体的想象转变成一种类似于文学的想象,话语和言语变成了文学式的文本,即言语,话语,语言之间的区别变得格外模糊,阅读者被安置在真实和虚构的边界中,此刻文学中的文字如同一面镜子,它作为一种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然而文学的想象是属于个人的,是充满差异的,是文化的和社会的。
随着意识形态的陨落,“现实,是不可能的”[2],真实是属于每个人的真实,观者必然依赖于主观化的想象来“创作”一个没有肉身的主体和主体所在的场景,我们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巴尔扎克的年代,我们需要通过语言去描述一个场景,而不是通过一个具象的图像去想象一个场景。并且为了给一个不存在的主体的话语限定一个场景,舞台上的小屏幕中给出了话语的来源地,它提供了说话者的情景和场所,这给观者的想象提供了一定的“语境”,这能让观者在差异的想象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共性理解。

除了基于文本内容的想象外,该戏剧还发展了一种不可理解性的文字,一方面体现在不同录音所产生的文字的意义中断上,录音和录音之间缺乏关联性,另一方面该戏剧还故意将词语分解,于是说话者的话语退化成一种难以理解的声音,例如在录音片段:一段先锋表演 (Une performance d’avant-garde) 中,该录音中约翰凯奇以中国《易经》为灵感,将原本具有特定含义的词句逐渐分裂成不连贯的词,甚至是直接将词分割开来,让词变成一场“空话”的表演。语言的瓦解切断了逻辑,于是这些“语言”就如同音乐一般被建构起来,“其结果是一种具体的诗歌,一个随机的乐谱”[3],语言成为一种主角,散落在各地成为了“声波的残留物”[4]。于是这种缺乏关联的文字在分解和拼贴中,在一种不可理解性中被观者解读,它依靠的正是观者的想象力。在此意义上,发声者变成了发音者,远离了一种叙事性的表述,而迈向了一种由抽象的文字、声音、图像共同完成的极简主义运动。
二、视觉的想象
这部戏中的视觉想象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图像,相反它是呈现了一个需要被想象的“文字图像”,即艺术家拒绝以摄影的方式或视频的方式呈现一个对现实世界的“复制”图像。并且这个文字图像不仅是为了给戏剧提供一个有效的视觉环境,而且是为了提供一个“拟人化”的人物形象,这些文字一方面作为一种主体性话语,另一方面则作为一个话语者的虚拟化的身体而存在。
因为剧中的文字图像是空间化的,首先它会改变位置,艺术家故意制造了一个具有体积的舞台,并将文字图像投影到三维空间内从而制造了一个位置关系,于是当文字图像的位置移动时,就如同一个说话者的身体的运动,观众可以展开对说话者行动的想象 ;其次,它会随着语言的声量或语气强调程度的变化而改变大小,当音量大时或强调程度加强时,图像会增大,说话者的存在感也被加强,反之则相反,于是文字图像模拟了人物的情绪,尤其是文字图像还包括了标点符号的图像,当出现感叹号的图像时,观者自然会了解到人物激动的情绪,它在某种程度上给一个“空位主体”提供了性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观者可以通过一个文字图像想象说话者的身体和个性,它使得观者对于该特殊的戏剧“表演者”的想象更加丰满,同时其非具象的特征使得想象差异化和开放化。

视觉形象的塑造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图像上,还表现在灯光和烟雾的使用上。在该戏剧中艺术家最常用的是聚光灯效果,尤其是当录音材料中出现一个“演讲者”形象的时刻,聚光灯朝向一个文字图像,三棱锥型的灯光在雾气中呈现出三维状态,仿佛是一个三维的肉身的在场,它加剧了观者对说话者身体的想象。其次,艺术家善于采用彩色的灯光,它不仅增加了视觉效果的丰富性,而且跟随着发言者的情绪而产生变化,或者说加强了“表演者”的情绪表达,并塑造了表演者所处的时空场景。
例如在片段:来自圣地亚哥的一部电影(Un film de San Diego)中,舞台中心先出现一个黑洞,中心白色微光逐渐转向紫红色和红色的交替,配合着录音中传来的女人的呻吟声和哀求男人的声音,它展现了一个做爱的场景和分手的场景的交替,一方面艺术家玩弄了原本的声音,用蒙太奇的方式重塑了声音的叙事,将不同场景通过声音联系在一起,最浓郁的激情和最痛苦的分离呈现了爱情的两个极端面貌,另一方面让观者以断裂式的想象去体会一个爱情的场景,即从一个想象到另一个想象的“跳跃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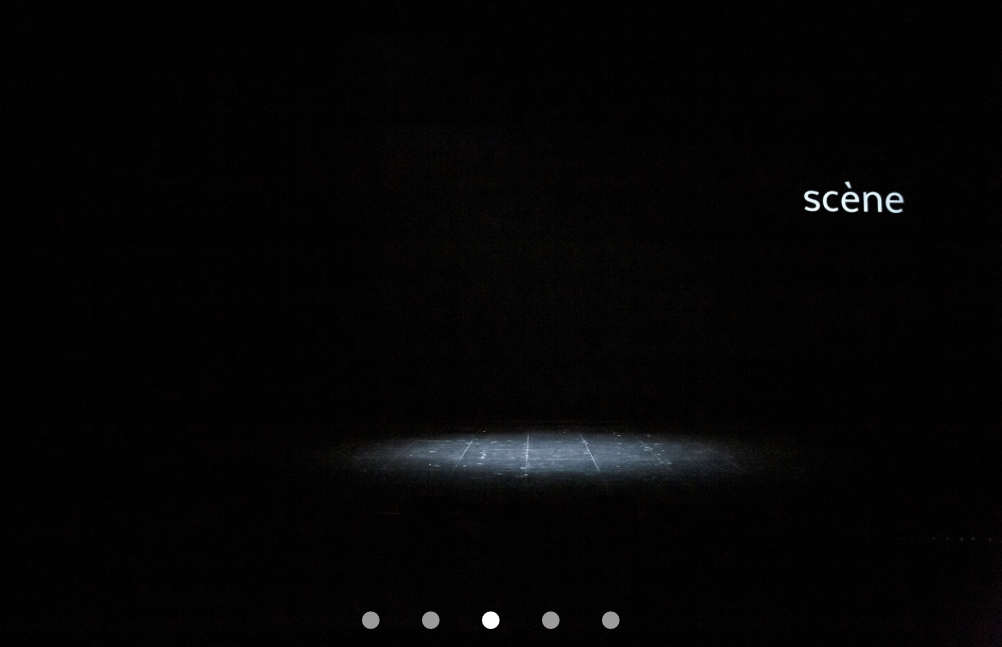
另外烟雾的使用也是特别的,烟雾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对一个消失的鬼魂的身体的隐喻,它为一个“空位主体”提供了一个可见的视觉形象,例如在录音片段:降神会(Une séance de spiritisme)中,烟雾溢出了屏幕,弥漫到观众席,它如同一个流动的却实体化的灵魂,逐渐地要抓住观者的身体,此刻观者不仅对鬼魂的形象展开想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从视听体验迈向了一种触觉体验。并让观者对那些过去的,甚至是消失和死亡的人产生了一种情感链接。我们触摸到烟雾,就如同我们触摸到那些缺席的半透明的身体。烟雾另一方面根据《新媒体剧作法》 (New Media Dramaturgy) 的作者所言,我们对于“雾”的理解应该脱离人类中心主义,它不一定是拟人性的,它作为一个制造氛围剧场的重要手段,它拥有自己的特殊的生命。“为了接受某物有能力,在不同程度上自主行动或运作,我们不需要把它解读为具有人类的特征。例如,我们不需要承认旋转的烟雾是一个行为者,只是承认像烟雾这样的东西有它自己做事的方式,而我们人类可能并不总是能够控制”[5],烟雾如同一个流动的主体,做着一个不可预知的行动,它可以无视舞台上的任何信息和任何人,也可以与观者产生互动的关系。它在观者的想象中成为了超出其自身的意义,一方面烟雾玩弄了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它让一些文字图像变得模糊,这种可见与不可见是政治性的,它暗示着我们世界对一些话语的强调或掩盖,另一方面它让观者在互动中重新注意到消失和转变的感觉,它提供了一种诗意的场景,让观者在其戏剧性的行动中发现时间的意义。

三、听觉的想象
赛丽亚-多特(Cyrielle Dodet)曾说:古往今来,声音凝结了许多幻想。它既扎根于身体,又位于身体之外,甚至可以具有神圣的品质。它可以是欺骗性的,或者相反,可以让人了解存在。[6]
该戏剧可以被认为是一场玩弄声音的戏剧,一场语言与音乐的辩论场。一方面声音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抽象存在,将存在本身转换为“存在的概念 (Fiction of presence) ”[7] (179),另一方面“声音确实可以识别一个地方,一种文化,一个现场的事件,但它的中间性和移动性可以从许多人中构成,并代表一个混合体”[8],这预示着声音暗示了一个移动的空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性,文化性以及开放性。正是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展开了一场声音的游戏,在不同形式的声音的再生产,即录音的再生产,现场演奏,现场配音的共同作用下,录制的声音和身体分离实现了一场存在与缺席的游戏,它们可以激发皆然不同的想象模式。
(一) 沉浸式声音
第一种声音类型是沉浸式的声音,这种声音追寻一种“真实性”,它激发了观众对于真实的场景的想象。例如在录音片段:俄罗斯莫斯科地铁的语音录音(Voix enregistrée du métro, Moscou, Russie) 中,首先灯光在观众席上从右扫到左,让观者沉浸式体验到进入地铁中的感觉,而后出现的地铁行驶时的噪音和地铁内的人物对话,促使观者从地铁外部通往车厢内部,此时声音是空间性的,它帮助听者实现了空间的转换。正如让-保罗-奎纳克(Jean-Paul Quéinnec)和安德烈-安妮-吉古尔(Andrée-Anne Giguère)所言:倾听的理解包括寻找身体、空间和声音直接的联系[…]当我们试图在空间中理解一个声音时,我们的整个身体都在移动,我们所有的姿态能力—听觉、视觉、触觉、动觉—以及我们所有的想象力都投射到它。然后一个空间被构建在一个相互的运动中:我们走向声音,它也走向我们[9]。
因此声音不仅调动了我们整个身体的体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触发一种通感,它连接了一种图像的想象,或者如罗伯特默里谢弗所言的形成了一个“声音图景” (soundscape),地铁内的噪音作为该声音片段的“调性”,即背景声音,人物对话作为一种激发人注意力的“声音信号”,最开始和最终地铁驶过的声音会作为一种“声音印记”存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一切都勾连着我们对于地铁场景的个人记忆,这些记忆会与该片段中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符号和沉浸其中,另一方面我们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声音片段中。因而观者的想象虽然是根据声音的,但是永远不会与其相同,说话者的声音是由其产生,但是并不属于它,“它属于空间[…]从演员中分离出来”[10]。
(二) 模仿性声音
第二种声音类型是模仿性的声音,它主要体现在音乐家们通过现场演奏乐器去模仿文字声调上,例如在录音片段:听障人士的语音专家(Experte vocal d’un malentendant)中,发音者在练习音标的读音,而音乐家利用小提琴声模仿其音调,一方面它揭露出音乐与语言之间的隐性关联,语言由音标组成,然而音标是还未形成语言的非语言,音乐正是在该意义上与语言同根。该片段如同一首拟声诗,重要的是说话的方式而不是内容,这帮助听者搭建音乐与语言之间的某种联想能力。另一方面音乐对语调的模仿,加强了语气,激发了一种情感语言的诞生,或者如马尔登-奥瓦迪亚(Malden Ovadija)所言:音调和声音[它们]源于痛苦、出生、死亡、狂欢的悲剧性尖叫[…],超越语言表达情感[11],这一点在录音片段:一位议员的发言(Intervention d’une députée du parlement) 中更加明显,文字图像随着说话者的口吃情况而发生改变,文字图像会等待声音,暗示这个人难以发言的窘境和其坚韧的性格,她必须证明自己同时坚定着完成发声的行为。现场的乐器声会切割人声,仿佛在模仿人的结巴的感觉,它为声音断句,促使那些我们看不见到情绪可以被听见和被想象。同时模仿意味着不同,乐器音与语言的声音仍然保留着自身的独立性,但是又受到彼此的“污染”。

(三) 异质性声音
第三种声音类型是异质性的声音,它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由于该戏剧中的声音来源众多,有录音,有现场乐器演奏的声音,有乐者的配音,声音的复杂性导致听者丧失了听觉中心,或者听者为了注意和理解某一个声音而无意识地忽略掉一些声音,例如在录音片段:天体生物学视频(Une vidéo d’astrobiologie)中,“演讲者”在诉说着关于天文学和占卜学的发言,音乐家同时发出“ei ” ,“o”的声音,如同一个遥远的回声,和对死者的呼唤。如果观者没有意识到声音是来自音乐家,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该声音是录音中传来的,这种无法辨认声音来源的异质感受会让听者必须选择聆听某一个主要的声音,它不仅导致空间的关系感加强,同时很可能让声音中的内容的意义失效,让其表达的方式成为主角。

例如在录音片段:不知名的古老佛教祈祷词的发音教程(Tutoriel de prononciation d’une prières bouddhistes vieu inconnu)中,日莲佛教的诵读被成倍的复制,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文字图像发生了快速漂移,它们迅速出现又迅速消失,一方面这隐喻着现实世界中信息出现的速度,很多信息还未被了解就消失在视野中,人们的注意力就是快速集中又快速转移的,另一方面当声音越来越多,它们变得越来越不可分辨,无法识别,这就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的现状。过载的话语和信息不仅让信息接受者无法完全获得完整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只能是片面的,这正是当今媒体传播的情景,听觉想象的爆炸导致了听觉的“失灵”,在另一层面上它也暗示着一种权力关系,结合所有录音而言,只有权威话语才有可能被听见。该异质性的声音片段真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理解和辨认其诵读的内容,而是反思当代声音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权力。
其次现场演奏的音乐除了给原本的录音配音外,它还有一种改变原本声音的功能。例如在录音片段:天主教传教(Un prêche catholique)中,音乐增强甚至改变了语言的节奏,让原本宗教说教变得如同一场现场说唱,它几乎改变了原有的语言语境,一方面以声音重新诠释文字,让人在录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想象中分裂,同时强调音乐与语言的关系,即音乐和语言共同的运动,另一方面它促使人们改变了对于宗教说教情景的想象,它必然是具有批判意味的想象。

最后声音的异化感还来自于声音与文字,图像的割裂感,三种不同的叙事媒介在该戏剧中不一定处于一种对话关系,相反它们很可能是辩论或竞争关系,且每一种不同的媒介都能确立各异的观照世界的方式,这意味着观众只能在该戏剧中选择集中注意力到某一个媒介,而无法直接在所有媒介的和谐中构建理解。文字与声音的抗争在于,该戏剧采用的录音片段来自世界各地,一方面它激发了我们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主体的不同构想,因为“那些讲几种语言的人知道,每一种语言的身体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每一种语言都预设了自己的发声体”[12](151)。这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依赖声音的特点来构想一个发声主体的身体,该身体依赖于每个文化和社会所给予听者的记忆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人无法仅通过声音来理解声音的意义,对不了解的语言,我们必须依赖翻译,即依赖文字图像中出现的法语,当我们优先处理可理解的图像媒介时,声音就丢失了一部分的听者的注意力,原声给予听者的印象会远远没有图像深刻。此时文字图像会成为观者的视觉中心,即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一个“不可见的身体”。
那么观者在体验这出“幽灵戏剧”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不断徘徊在视觉中心化和各种媒介共存的去中心化之间,每个观者都在一边选择一边解读,这意味着该“戏剧模糊了参考点,特别是当感官知觉的所有维度都被调用,以引起对多个符号的注意,这些符号本身同时提供了多个视点”[13],这将观者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戏剧体验。而声音和图像的分裂体现在舞台空间和广播空间的不和谐上,例如在录音片段:传统歌曲—Pile de Barra (Chant traditionnel Pile de Barra) 中,它展示了一种“口腔音乐”(Musique à bouche),它听上去如同失真的变速的声音,且声音来自剧场的右侧,但是文字图像却出现在屏幕的左侧,这导致了对于说话者存在性感知的错位,一方面它切断了观者的沉浸感,另一方面它暗示着对世界上话语来源的真实性的质疑,加强了戏剧的反思性。
艺术家对于声音的玩弄似乎总是在发展一种媒介间的分裂且共存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戏剧舞台可以被称为一个装置(dispositif),即“一组异质的元素”和“在这些元素之间建立的网络”[14],每一个媒介都作为一个对现实世界的中介,我们“不再一定寻求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不再寻求在每个媒介之间创造互动”[15],它们只是一起邀请观者的介入,作为一个通往想象世界的钥匙,该世界中的内容完全由我们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导演“不再负责协调整体,而是负责模糊界限”[16]。那么这个不断变异又相互关联的戏剧系统会最终通往一个混合的,互动的空间,它会彻底促使观者的感知体验和想象力的倍增。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们完全取消了戏剧的“故事性”或者说“叙事性”,事实上该戏剧的所有媒介的差异化和断裂性都从属于该戏剧的主题,即不同主体的,不同形式的差异性话语的相遇和交流。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开头的哈姆雷特的录音片段,关于罗马宫殿壁画介绍的录音片段,以及最后一段录音片段:在YouTube上发布的告别视频(Video d’adieux postées sur YouTube)中。开头的哈姆雷特与鬼魂的对话为观众提供了一条想象的路径,即这是一场关于召唤鬼魂的戏剧;罗马宫殿壁画介绍的片段则提醒观众要通过图像去想象“鬼魂”的形象;之后所有的片段都在展现不同地点以及不同形式的声音所制造的“鬼魂”的声音;直到最后一个录音,它才向观者解释了这场的戏剧的意图,通过艺术家们对录音的再生产,促使录音的内容既属于原本语境又逃离和超越原本语境来为戏剧叙事服务。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录音中的声音与观者直接对话,它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走进自己的责任,以团体的形式做决策,说明了我们的民主应该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从这一刻起观者的目光转化成为见证者,见证了一次全球性话语的交流过程,尤其是在该片段中沉默和声音成为了一对“情侣”,沉默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声音为见证者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反思时刻,“无论是期待的时刻,还是倾听被意外打断的时刻,或是精神共鸣的时刻,沉默都说明了我们的倾听”[17],艺术家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迫使观者以倾听的方式来介入戏剧。
一方面观者通过将这次交流活动中世界性的话语纳入到自身的话语体系中从而成就了一个新的自我,另一方面观者强制性地与最终的录音开启一场对话,它链接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每个人提供了自己的视点,在克里斯蒂安-比埃特(Christian Biet)和克里斯托夫-特里乌(Christophe Triau)这里:这种同时性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的优点是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唤起观众的身份:社会个体 [18]。于是在所有人的共同叙事下促成了一股调解的力量,这出戏剧会作为一场差异话语的调和剂完成一次社会干预,同时促使观者的想象具有了某种共性。
结语
总的来说,该作品的艺术家们通过将文字-图像-声音,三种不同的媒介平等地整合成一个异质性的整体,在观者的想象中它们被塑造成一群缺席的“表演者”,他们既是他们自身同时又在观众的共同叙事中超出其自身的意义。在艺术家们的再生产和蒙太奇手段下,导致了真实和虚拟的不可区分性,如迪迪-胡伯尔曼(Didi-Huberman)所言:蒙太奇作为他的诗学的一个基本元素出现,[…]是任何重新组合的条件,不是为了呈现真实,而是为了暴露其真相,或者说为了呈现真实的问题,也就是暴露其关键点、其缺陷、其失调[19],在此意义上,其“虚构性”反而证明了某种真实性。
一方面该戏剧不是由戏剧情景构成的,而是观众的审美视野和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三种媒介所造成的三种层面的想象是在无意识中被关联,被忽略,被中断的,它催化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想象剧场,即对一个世界性的交流场景的想象,其核心目的是促进差异话语之间的调解和观众的反思,通过诉诸感官去激发不同层面的智力。在此意义上该戏剧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自传式和疏远式共存的参与体验,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因为人们无法思考不存在的东西[…]对思考者来说,这些东西不是‘不存在’,它们参与到存在之中”[20]。于是这些“表演者”和观众都被联系在一起,一起促成了一个被改写的历史,观众也在这种对缺席的身体的感知中“无限地意识到每个人的独特性以及他们的脆弱性”[21]。
参考文献:
[1] [7] [12] Directeur of Josette Féral, Pratique performatives : Body Remix, sous la direction de Josette Féral, Édition de Presse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et d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2.
[2] Françoise Lavocat, Fait et fiction : pour une frontière, Édition du Seuil, mars 2016, p.118.
[3] [4] [11] Malden Ovadija, Dramaturgie du son : la matérialité de la voix et l’architecture du son / bruit dans le théâtre de Romeo Castellucci et de Robert Wilson. L’Annuaire théâtral, (56-57), 2014, p. 47–57. https://doi.org/10.7202/1037327ar
[5] Peter Eckersall, Helena Grehan, Edward Scheer, New Media Dramaturgy : Performance, Media and New-Materialism, Édition d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84.
[6] [17] Cyrielle Dodet, Le théâtre mis sur écoute : écho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 « Le son du théâtre ». Jeu, (147), 2013, p.144–149.
[8] [16] Jean-Paul Quéinnec, Dispositif cartographique du son pour une scène sans bord. Recherches sémiotiques / Semiotic Inquiry, 36(1-2), 2016, p.271–294. https://doi.org/10.7202/1051188ar
[9] Jean-Paul Quéinnec, Andrée-Anne Giguère, À l’écoute d’une textualité performative : l’expérience de Phonographie maritime. Percées,2019, p.1-2. https://doi.org/10.7202/1075188ar . Marcel Freydefont, « Les contours d’un théâtre immersif (1990-2010) », Agôn, n ° 3, 2011, journals. doi : https://doi.org/10.4000/agon.1559
[10] Michel Chion, Le son : traité d’acoulogie, Édition d’Armand Colin, 2010, en version électronique, p.16-17.
[13] [14] [15] [19] Jean-Paul Quéinnec, De l’informe à la dramaturgie sonore au théâtre : le devenir ouvertement déclassé et enjoué d’une scène sans bord. L’Annuaire théâtral, (62), 2017, p.95–116.
[18] Christian Biet, Christophe Triau, Qu’est-ce que le théâtre? Éditions de Gallimard, 2006, p.62.
[20] Claude Maritan, Présence et absence, Éditions Campagne Première, « Les lettres de la SPF », 2007/2, numéro 18, p.73-82.
[21] Emmanuelle Lequeux, « Personnes au Grand Palais » in Christian Boltanski. Monumenta 2010/ Grand Palais, (Paris : Beaux Arts éditions/TIM éditions, janvier 2010), p.7.
作者:杜静怡,巴黎新索邦大学戏剧专业研究生(预博士生);LIRIS (图像与场景学/舞美艺术国际研究实验室) 核心成员。
责编:LULU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