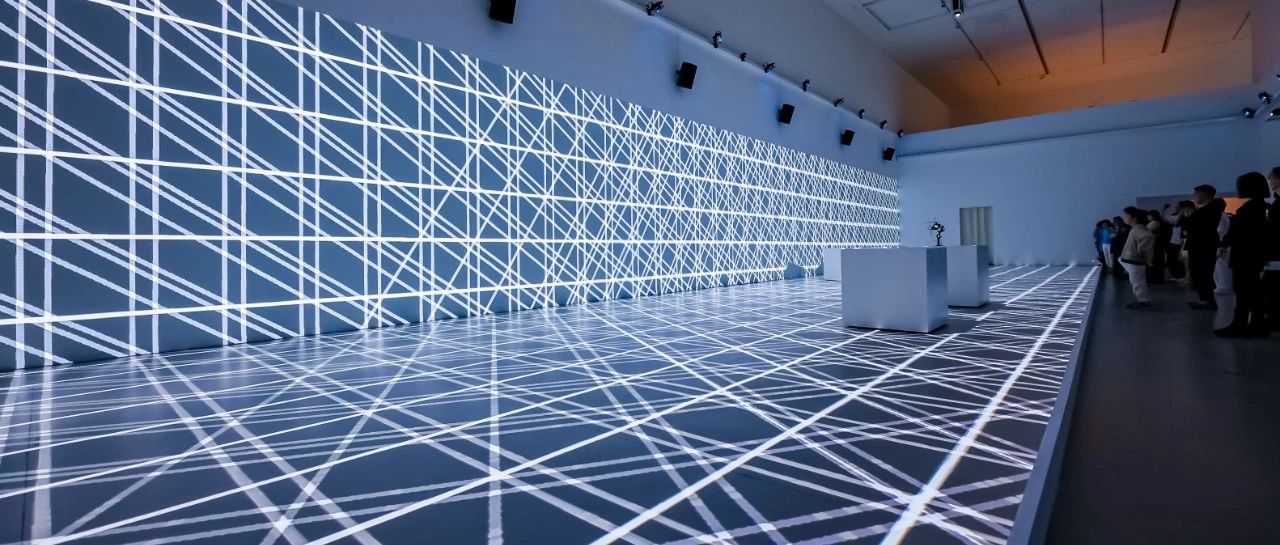美国加州洛杉矶,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Lucas Museum of Narrative Art)鸟瞰渲染图,由马岩松及MAD建筑事务所设计。图片来源: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美国加州洛杉矶,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Lucas Museum of Narrative Art)鸟瞰渲染图,由马岩松及MAD建筑事务所设计。图片来源: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三 年前的2020年,当世界深陷在新冠疫情的时间里,我与一些艺术博物馆馆长对博物馆未来的进化方向进行了对谈。这些对话被收录在《博物馆的未来:28次对谈》中,探讨了博物馆如何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在这些变化中,博物馆更新了它们的软件系统——变得更开放、包容、热情、鼓励参与、技术娴熟、重视社区又放眼全球。但同时,一座通过这种新软件系统运行的博物馆也会需要新的硬件,这也是我选择在2022年春夏两季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交流谈话的原因。
新博物馆,柏林。图片来源:© SMB / Ute Zscharnt for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如果你有和我相似的成长经历,你大概不会对宏伟壮观、散发着权威气息的博物馆,以及与这种权威感相得益彰的建筑感到稀奇。这些博物馆建筑多是希腊神庙式的,即使是对我这个欧洲人来说,也暗示着一种强势的文化联系。从走向入口的路开始,参观博物馆便如同一趟朝圣之旅。你总得爬上一座小山或几段台阶才能真正到达大门。里面有守卫监视着大家的一举一动。“观赏艺术”意味着静静地从一件作品走到另一件作品,凝视它们——仿佛这样便能透过一系列带框的窗口,进入美学的崇高境界,这是对于朝圣的奖励。即使博物馆在20世纪被搬进了更为现代的建筑,也仍保持着一种冷静克制的风格,在今天则多是由混凝土和棱角分明的极简主义风格的组合来进行呈现。而画廊——被消减到只剩下四面白色的墙壁——则被严格保留用于与艺术的邂逅。这些令人感到肃然的白盒子进一步强化了艺术与生活泾渭分明的固有文化现象,它们也是神圣式建筑在艺术博物馆中留下的遗迹。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图片来源:Photo by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游客在累了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休息的地方。馆内的长凳通常由硬木或石料制成。设施很简陋。博物馆周围的绿地也都是后话了。这种环境中的一切都在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文化要被认真对待;它全是严肃工作,没有娱乐。但随着艺术博物馆的排他性氛围逐渐削弱,开始要根据入场观众的规模来衡量成功,事情发生了转变。与之相应地,博物馆建筑也换上了新装。早在1934年,布鲁克林博物馆就做出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决定,拆除通往由McKim, Meade & White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大楼入口处的楼梯,以使博物馆让人感到更“民主”。许多高大庙宇式博物馆都争相效仿。动荡的1960年代为文化民主带来了新动力,巴黎获益颇丰。到了1977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创立,直截了当地宣布博物馆和城市街道之间不再需要边界。又七年后,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落户”卢浮宫前庭院,而现在的卢浮宫不仅吸引了所有人,这座玻璃金字塔更成为了博物馆的标志。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图片来源:Photo by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游客在累了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休息的地方。馆内的长凳通常由硬木或石料制成。设施很简陋。博物馆周围的绿地也都是后话了。这种环境中的一切都在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文化要被认真对待;它全是严肃工作,没有娱乐。但随着艺术博物馆的排他性氛围逐渐削弱,开始要根据入场观众的规模来衡量成功,事情发生了转变。与之相应地,博物馆建筑也换上了新装。早在1934年,布鲁克林博物馆就做出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决定,拆除通往由McKim, Meade & White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大楼入口处的楼梯,以使博物馆让人感到更“民主”。许多高大庙宇式博物馆都争相效仿。动荡的1960年代为文化民主带来了新动力,巴黎获益颇丰。到了1977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创立,直截了当地宣布博物馆和城市街道之间不再需要边界。又七年后,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落户”卢浮宫前庭院,而现在的卢浮宫不仅吸引了所有人,这座玻璃金字塔更成为了博物馆的标志。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STAN HONDA/AFP/Getty Images20世纪后期,博物馆建筑进入超速发展阶段。一时间,华丽的设计开始盛行,以1997年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为顶峰。该建筑因使用其所在城市为设计元素而倍受赞誉,但其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超越了建筑层面的内容,以毕尔巴鄂这座城市为舞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这也是自从1959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在第五大道上以明亮且引人注目的白色“开瓶器”造型开馆以来,人们再一次因为博物馆的建筑蜂拥而至。委托知名建筑师建造标志性博物馆建筑的方法,被证明是具有文化需求的城市发展的制胜法宝。随着中国和海湾石油国家在千禧年后纷纷兴起博物馆建设热潮,“明星建筑”时代产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作品,不仅起到了吸引游客的作用,也是国家现代性的象征。然而,这种模式的结果可谓毁誉参半。它似乎是用另一种权威语言代替了之前的模式,只是稍微不那么令人生畏了——虽然不再用科林斯柱式,却都有闪闪发光的玻璃;不再用意大利大理石,却开始用稀有金属。希腊神庙和大理石覆盖的现代主义城堡已从文化权力的金字塔尖走向衰落,而新的建筑奇观则成为许多人心中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及根植于这一新秩序的不平等鸿沟的化身。当其他“高级”艺术形式举步维艰时,充满活力、无比自信的建筑确实有助于快速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但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博物馆并不一定有益于其中展示的艺术品。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开始觉得这些诱人的建筑不是为他们设计的。当然,明星建筑并不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产生的唯一一种博物馆设计模式。几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调和艺术博物馆身上大众性特质和精英主义脉搏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建筑师们还是逐渐意识到,吸引人们进入艺术博物馆的策略其实是在把相当一部分公众拒之门外。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STAN HONDA/AFP/Getty Images20世纪后期,博物馆建筑进入超速发展阶段。一时间,华丽的设计开始盛行,以1997年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为顶峰。该建筑因使用其所在城市为设计元素而倍受赞誉,但其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超越了建筑层面的内容,以毕尔巴鄂这座城市为舞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这也是自从1959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在第五大道上以明亮且引人注目的白色“开瓶器”造型开馆以来,人们再一次因为博物馆的建筑蜂拥而至。委托知名建筑师建造标志性博物馆建筑的方法,被证明是具有文化需求的城市发展的制胜法宝。随着中国和海湾石油国家在千禧年后纷纷兴起博物馆建设热潮,“明星建筑”时代产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作品,不仅起到了吸引游客的作用,也是国家现代性的象征。然而,这种模式的结果可谓毁誉参半。它似乎是用另一种权威语言代替了之前的模式,只是稍微不那么令人生畏了——虽然不再用科林斯柱式,却都有闪闪发光的玻璃;不再用意大利大理石,却开始用稀有金属。希腊神庙和大理石覆盖的现代主义城堡已从文化权力的金字塔尖走向衰落,而新的建筑奇观则成为许多人心中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及根植于这一新秩序的不平等鸿沟的化身。当其他“高级”艺术形式举步维艰时,充满活力、无比自信的建筑确实有助于快速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但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博物馆并不一定有益于其中展示的艺术品。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开始觉得这些诱人的建筑不是为他们设计的。当然,明星建筑并不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产生的唯一一种博物馆设计模式。几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调和艺术博物馆身上大众性特质和精英主义脉搏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建筑师们还是逐渐意识到,吸引人们进入艺术博物馆的策略其实是在把相当一部分公众拒之门外。 音乐之家,匈牙利布达佩斯,由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所(Sou Fujimoto Architects)设计。图片来源:由György Palkó摄影,© LIGET BUDAPEST正如博物馆领导者寻求向更广、更多元的观众开放场馆一样,建筑师们也开始不再追求那种突出自己的“表达式设计”,转向更受欢迎、更平易近人的博物馆设计风格,通过设计理念将自身深深扎根于所在的社区和城市或自然环境中。建筑艺术,与许多其他艺术一起,保持了与艺术界新态度一致的转变。即使是设计过标志性博物馆的建筑师也转向了更克制和深层的解决方案。如今,建筑领域已经普遍认为“明星建筑式”博物馆的时代已经结束。其中一位建筑师在谈话中说“会摇摆不定”,另一位说“好的建筑不一定是昂贵的,或外型一定要如何壮观”,第三位则说“我真的不喜欢博物馆设计的‘吸睛’比赛”。这些发言都在说明,大家认为应当尽量避免这种标志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设计,或者把设计目的单纯设想为构建令人感到敬畏的空间。建筑师们也对自我标榜的、掩盖博物馆与殖民主义残留之间的联系的那种移花接木式建筑表示鄙夷。今天的建筑师正在寻找“更好的建筑方式”,一个通往“非纪念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非亮眼结构的支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建筑不令人惊叹”,一位明星建筑师说,“但最近一代的建筑已经发生了转变。”简而言之,博物馆建筑和博物馆本身一样,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建筑师正在重新调整目的和方法,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创造能满足当下社会需求的、包容的文化空间。总的来说,博物馆建筑正在脱离被设计成“世俗化世界教堂”的传统,但仍渴望以一种不那么神圣或等级森严的语言来建立类似的印象。不管怎样,建筑师们正在努力平衡张扬与内敛之间的度。他们希望创建出这样的建筑——能容纳所有阶层的公众,并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服务艺术和社会的重要公共机构。如果一切向好,此类年轻的博物馆建筑将成为新兴21世纪博物馆学的成长伙伴。答案掌握在建筑师手中。从2022年3月到2022年9月,我与25位建筑师进行了坐谈,一起探讨未来的博物馆。我既不是建筑评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是正在寻求记录那些可能出现的共识。
音乐之家,匈牙利布达佩斯,由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所(Sou Fujimoto Architects)设计。图片来源:由György Palkó摄影,© LIGET BUDAPEST正如博物馆领导者寻求向更广、更多元的观众开放场馆一样,建筑师们也开始不再追求那种突出自己的“表达式设计”,转向更受欢迎、更平易近人的博物馆设计风格,通过设计理念将自身深深扎根于所在的社区和城市或自然环境中。建筑艺术,与许多其他艺术一起,保持了与艺术界新态度一致的转变。即使是设计过标志性博物馆的建筑师也转向了更克制和深层的解决方案。如今,建筑领域已经普遍认为“明星建筑式”博物馆的时代已经结束。其中一位建筑师在谈话中说“会摇摆不定”,另一位说“好的建筑不一定是昂贵的,或外型一定要如何壮观”,第三位则说“我真的不喜欢博物馆设计的‘吸睛’比赛”。这些发言都在说明,大家认为应当尽量避免这种标志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设计,或者把设计目的单纯设想为构建令人感到敬畏的空间。建筑师们也对自我标榜的、掩盖博物馆与殖民主义残留之间的联系的那种移花接木式建筑表示鄙夷。今天的建筑师正在寻找“更好的建筑方式”,一个通往“非纪念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非亮眼结构的支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建筑不令人惊叹”,一位明星建筑师说,“但最近一代的建筑已经发生了转变。”简而言之,博物馆建筑和博物馆本身一样,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建筑师正在重新调整目的和方法,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创造能满足当下社会需求的、包容的文化空间。总的来说,博物馆建筑正在脱离被设计成“世俗化世界教堂”的传统,但仍渴望以一种不那么神圣或等级森严的语言来建立类似的印象。不管怎样,建筑师们正在努力平衡张扬与内敛之间的度。他们希望创建出这样的建筑——能容纳所有阶层的公众,并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服务艺术和社会的重要公共机构。如果一切向好,此类年轻的博物馆建筑将成为新兴21世纪博物馆学的成长伙伴。答案掌握在建筑师手中。从2022年3月到2022年9月,我与25位建筑师进行了坐谈,一起探讨未来的博物馆。我既不是建筑评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是正在寻求记录那些可能出现的共识。 Saradar收藏馆开放式仓库的室内大厅景观,Mar Shaaya,黎巴嫩。图片来源:© Lina Ghotmeh - Architecture而这个共识真的出现了。虽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建筑师都想法相似,但他们的确在一些基本原则上保持了一致。他们都热切相信博物馆应被归类到文化和建筑的领域,并同样迫切地渴望重新思考、做出改变。“要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文化建筑的设计师说,“博物馆不能被视为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普遍的必需品。”然而,考虑到在当代的文化环境,有些建筑师补充说,“还必须能接受自我批评和矛盾。”“如果博物馆建筑不进化”,另一位也警告说,“博物馆将会变成一种被淘汰的建筑类型。”与我交谈过的不少建筑师都决心打破博物馆传统的形式、等级和不可渗透性。他们不谋而合的信念包括透明的、包容的和开放的结构——总结来说,他们希望设计“没有边界的博物馆”。建筑师希望更多看到一个内外连续的统一体,打破博物馆展览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分界线。他们盼望为“灰色空间”或“中间地带”注入活力,比如公园和绿地,以及建筑物内的“口袋空间”(pocket spaces),为它们提供广泛、多维的学习、集会、反思和放松的环境。博物馆被视为“第三空间”,一个既非工作环境也非家庭环境的,日常生活发生的场所。建筑师更是提出了一种“流动”的建筑构想,让艺术充满整个博物馆,让生活畅通无阻地流动在其庄严的空间中。在这些建筑师看来,博物馆应该能“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摆脱“博物馆是单一功能建筑”的想法。为响应最近博物馆学思想的转变,他们将博物馆想象成一个表演空间,参观者——作为舞台上的演员——有权控制行动。有好几位受访者谈到要将更多主动权移交给参观者,让他们从繁重的策展介入中解放出来,自主规划在建筑物中的旅程。“灵活性”可能是我在谈话中听到最多的词。
Saradar收藏馆开放式仓库的室内大厅景观,Mar Shaaya,黎巴嫩。图片来源:© Lina Ghotmeh - Architecture而这个共识真的出现了。虽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建筑师都想法相似,但他们的确在一些基本原则上保持了一致。他们都热切相信博物馆应被归类到文化和建筑的领域,并同样迫切地渴望重新思考、做出改变。“要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文化建筑的设计师说,“博物馆不能被视为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普遍的必需品。”然而,考虑到在当代的文化环境,有些建筑师补充说,“还必须能接受自我批评和矛盾。”“如果博物馆建筑不进化”,另一位也警告说,“博物馆将会变成一种被淘汰的建筑类型。”与我交谈过的不少建筑师都决心打破博物馆传统的形式、等级和不可渗透性。他们不谋而合的信念包括透明的、包容的和开放的结构——总结来说,他们希望设计“没有边界的博物馆”。建筑师希望更多看到一个内外连续的统一体,打破博物馆展览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分界线。他们盼望为“灰色空间”或“中间地带”注入活力,比如公园和绿地,以及建筑物内的“口袋空间”(pocket spaces),为它们提供广泛、多维的学习、集会、反思和放松的环境。博物馆被视为“第三空间”,一个既非工作环境也非家庭环境的,日常生活发生的场所。建筑师更是提出了一种“流动”的建筑构想,让艺术充满整个博物馆,让生活畅通无阻地流动在其庄严的空间中。在这些建筑师看来,博物馆应该能“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摆脱“博物馆是单一功能建筑”的想法。为响应最近博物馆学思想的转变,他们将博物馆想象成一个表演空间,参观者——作为舞台上的演员——有权控制行动。有好几位受访者谈到要将更多主动权移交给参观者,让他们从繁重的策展介入中解放出来,自主规划在建筑物中的旅程。“灵活性”可能是我在谈话中听到最多的词。 罗斯建筑事务所(Roth Architecture)设计的SFER IK - Uh May艺术中心,墨西哥。图片来源:Roth Productions这些建筑师将博物馆视为分享知识的“邂逅空间”(spaces of encounter),不仅需要“非常亲密”而且还要“非常有趣”。他们将博物馆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市民空间”、一个“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让人们接触到艺术和思想,但也让他们时不时地能“放慢脚步,集中注意力”,以摆脱无情的现代生活的“分心和快节奏”。在这种博物馆里,“一切都变得敏感,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然而,增强的体验并不是通过“空间的简朴和中性”来实现的。白盒子画廊是20世纪中叶的遗产,但它并不是答案。“展示艺术不需要白盒子,”一位受访者指出,这其实也是一个普遍观点,“白墙太原始”,也太受限了。博物馆体验可以“去中心化”,不仅是在单个博物馆建筑内,还有当它向外辐射,在成为“整个城市的卫星”时产生的与社区的关系上。建筑师们清楚如今正处于博物馆设计的过渡阶段,各种机构都受到质疑。他们非常警惕博物馆必须与当前“修正西方叙事和殖民叙事的历史时刻”保持一致——这一代际转变对机构的软件和硬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认识到,博物馆作为公共服务结构,必须站在气候行动的先锋。整个行业都需要面向未来。值得注意的是,气候意识涉及抑制博物馆对新建筑看似永不满足的胃口。一位建筑师宣称“盖房子不是前进的方向”。而另一位建筑师的话揭示了这代人的首要目标,他说:“我们需要始终将未来的建筑与自然联系起来。”
罗斯建筑事务所(Roth Architecture)设计的SFER IK - Uh May艺术中心,墨西哥。图片来源:Roth Productions这些建筑师将博物馆视为分享知识的“邂逅空间”(spaces of encounter),不仅需要“非常亲密”而且还要“非常有趣”。他们将博物馆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市民空间”、一个“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让人们接触到艺术和思想,但也让他们时不时地能“放慢脚步,集中注意力”,以摆脱无情的现代生活的“分心和快节奏”。在这种博物馆里,“一切都变得敏感,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然而,增强的体验并不是通过“空间的简朴和中性”来实现的。白盒子画廊是20世纪中叶的遗产,但它并不是答案。“展示艺术不需要白盒子,”一位受访者指出,这其实也是一个普遍观点,“白墙太原始”,也太受限了。博物馆体验可以“去中心化”,不仅是在单个博物馆建筑内,还有当它向外辐射,在成为“整个城市的卫星”时产生的与社区的关系上。建筑师们清楚如今正处于博物馆设计的过渡阶段,各种机构都受到质疑。他们非常警惕博物馆必须与当前“修正西方叙事和殖民叙事的历史时刻”保持一致——这一代际转变对机构的软件和硬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认识到,博物馆作为公共服务结构,必须站在气候行动的先锋。整个行业都需要面向未来。值得注意的是,气候意识涉及抑制博物馆对新建筑看似永不满足的胃口。一位建筑师宣称“盖房子不是前进的方向”。而另一位建筑师的话揭示了这代人的首要目标,他说:“我们需要始终将未来的建筑与自然联系起来。” UCCA沙丘美术馆鸟瞰图,秦皇岛阿那亚。图片来源:Photo by Wu Qingshan对建筑师来说,令人烦恼的一点是在不稳定的未来世界中,永久性结构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文化实体将需要不断“超越目前的职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博物馆适合未来。我也听说过一些惊人的原创概念,从可以实时定制空间以适应艺术品的建筑,到以做豆腐等乡村风俗为展示内容的博物馆,再到与自然遗址相协调的洞穴式文化空间,又或者是配备数字设备的建筑中可以通过轻按开关远程更改所参观博物馆的类型。今天的建筑师一定会被关于博物馆在全数字化社会中形态的对话所吸引。“所有机构都在与互联网时代的余波作斗争”,一位建筑师说,“这已经完全挑战了权威的单一性,并相应地迫使建筑重新思考如何为专家和公民之间搭建可信的互动空间。”在数字人工制品占主导地位的未来是否会允许或需要一个物理空间来组装和展示物理对象?换言之,明天的数字博物馆与今天的实体博物馆会有多大差异?尽管博物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建筑师们对其前景仍持乐观态度——只要它能够适应。他们相信建筑可以成为这种转变的催化剂。“我们确信博物馆是先驱,是前卫的一部分,”一位人士说,“不仅仅是艺术的先锋,也是社会的先锋。”需要澄清的是,与我交谈的建筑师中没有一个认为博物馆应成为某种“止痛药式的社区空间”。没有人提议将其中的展品抛开不谈,放弃博物馆的教育和研究功能,将其变成纯粹的娱乐场所。“一个满是荷兰黄金时代或法国印象派画作的房间不太可能发生太大变化,”一位建筑师说,“你还是要墙壁来悬挂它们,营造一个能欣赏它们的、可供沉思的空间。”
UCCA沙丘美术馆鸟瞰图,秦皇岛阿那亚。图片来源:Photo by Wu Qingshan对建筑师来说,令人烦恼的一点是在不稳定的未来世界中,永久性结构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文化实体将需要不断“超越目前的职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博物馆适合未来。我也听说过一些惊人的原创概念,从可以实时定制空间以适应艺术品的建筑,到以做豆腐等乡村风俗为展示内容的博物馆,再到与自然遗址相协调的洞穴式文化空间,又或者是配备数字设备的建筑中可以通过轻按开关远程更改所参观博物馆的类型。今天的建筑师一定会被关于博物馆在全数字化社会中形态的对话所吸引。“所有机构都在与互联网时代的余波作斗争”,一位建筑师说,“这已经完全挑战了权威的单一性,并相应地迫使建筑重新思考如何为专家和公民之间搭建可信的互动空间。”在数字人工制品占主导地位的未来是否会允许或需要一个物理空间来组装和展示物理对象?换言之,明天的数字博物馆与今天的实体博物馆会有多大差异?尽管博物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建筑师们对其前景仍持乐观态度——只要它能够适应。他们相信建筑可以成为这种转变的催化剂。“我们确信博物馆是先驱,是前卫的一部分,”一位人士说,“不仅仅是艺术的先锋,也是社会的先锋。”需要澄清的是,与我交谈的建筑师中没有一个认为博物馆应成为某种“止痛药式的社区空间”。没有人提议将其中的展品抛开不谈,放弃博物馆的教育和研究功能,将其变成纯粹的娱乐场所。“一个满是荷兰黄金时代或法国印象派画作的房间不太可能发生太大变化,”一位建筑师说,“你还是要墙壁来悬挂它们,营造一个能欣赏它们的、可供沉思的空间。”
大卫·阿贾耶(David Adjaye)设计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华盛顿特区。图片来源:© Nic Lehoux
建筑师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升级和进化。他们寻求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突出博物馆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有意义的体验,同时消除公众在进入博物馆时感到的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以使这些机构与当下的生活步调更加一致。这种思路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即博物馆属于所有人——在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去年修订的博物馆定义中,第一行文字就说“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人们希望在当今高度两极分化的公共生活中,也能有一个空间让各种信仰和各行各业的人走到一起,不管是抽象还是物理层面上。建筑师的任务是将这些理想转化为有形的、实用的形式。但如果仅靠建筑——在与遗留结构、要求苛刻的客户及场地和材料的物理限制抗衡的建筑——无法激发机构的全部能力。博物馆不应与其建筑相混淆,它远不止于此。但建筑可以做的,是帮助博物馆发挥出更大的潜力。因此,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在这些建筑物中运行的“软件”。事实是,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在一座平庸的建筑中也可以发挥作用,但再好的建筑也无法将缺乏强大艺术内核的博物馆变得伟大。为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博物馆建筑和博物馆本身一样将永远处于建造状态。如果建筑可以成为这一旅途的伙伴和向导,便算是尽其所长了。
*本文摘自András Szántó刚刚发布的新书《想象未来博物馆:与建筑师的21段对话》(Imagining the Future Museum: 21 Dialogues With Architects),内容经过了编辑与缩略。
文丨András Szántó
译丨Yunyi Yang

联系Artnet中国:xinxi@artnet.com


 美国加州洛杉矶,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Lucas Museum of Narrative Art)鸟瞰渲染图,由马岩松及MAD建筑事务所设计。图片来源: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美国加州洛杉矶,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Lucas Museum of Narrative Art)鸟瞰渲染图,由马岩松及MAD建筑事务所设计。图片来源: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图片来源:Photo by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图片来源:Photo by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STAN HONDA/AFP/Getty Images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STAN HONDA/AFP/Getty Images 音乐之家,匈牙利布达佩斯,由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所(Sou Fujimoto Architects)设计。图片来源:由György Palkó摄影,© LIGET BUDAPEST
音乐之家,匈牙利布达佩斯,由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所(Sou Fujimoto Architects)设计。图片来源:由György Palkó摄影,© LIGET BUDAPEST
 Saradar收藏馆开放式仓库的室内大厅景观,Mar Shaaya,黎巴嫩。图片来源:© Lina Ghotmeh - Architecture
Saradar收藏馆开放式仓库的室内大厅景观,Mar Shaaya,黎巴嫩。图片来源:© Lina Ghotmeh - Architecture 罗斯建筑事务所(Roth Architecture)设计的SFER IK - Uh May艺术中心,墨西哥。图片来源:Roth Productions
罗斯建筑事务所(Roth Architecture)设计的SFER IK - Uh May艺术中心,墨西哥。图片来源:Roth Productions UCCA沙丘美术馆鸟瞰图,秦皇岛阿那亚。图片来源:Photo by Wu Qingshan
UCCA沙丘美术馆鸟瞰图,秦皇岛阿那亚。图片来源:Photo by Wu Qing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