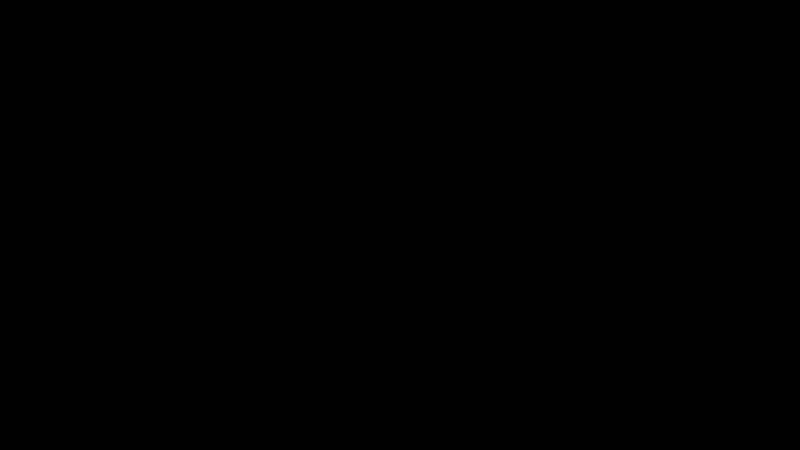策划:钟刚
编辑:梁丹如
“年度计划”是《打边炉》每年年初都会循例推出的专题,众多艺术工作者的回应,以地方为线索予以集结。
这是一项需要花时间联络沟通和整理的工作,其意义,并不在于构筑一部指南式的行动目录,“计划”只是一种切入的角度,艺术工作者们的日常行动、思考和言说,经由梳理,是一个塑造和肯定自身的过程。而这种寻找、收集、整理和保存,经过时间的累积,逐渐显出了“微观-档案“和”地方-图景“的意义。
这项工作依然在继续。今年,我们共邀请到36位在长三角地区生活的艺术工作者,围绕如下六个问题展开讨论。本文按中文姓氏首字母倒序排列,发表前经《打边炉》编辑部删选。
• 疫情三年,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你⼜如何在这个影响之下开始新⼀年的⼯作?• 随着年岁的增⻓,“时间”在你的⽣活和⼯作中意味着什么? • 在你的⼯作计划当中,是否有⼀件需要“下决⼼”去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
策展人,《碧山》杂志书主编
我没有被艺术抛弃,这让我有点高兴。事实上,从2011年起,我就离开了那个圈子。这三年因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手头的每一件工作随时都有延宕的可能。但乐观来说,我们的行动开始变慢了,不是那么着急地去完成一件事,留给思考的时间多了起来。从悲观的角度,嗯,好像我没那么悲观,坦然接受吧,这跟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有关。到了我这个年纪,时间是第一重要的,毫无疑问,拥有充裕的时间是奢侈的。并列第一的还有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时间。目前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越来越倾向于把一件事情“复杂化”,工作内容往往会溢出委托的范围,有一种“扎猛子”的感觉,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由于疫情的耽误,事情越积越多,给我们的团队造成了很大挑战。从去年开始,我有意识地让几个年轻人来主导一些工作,希望日后自己能轻松一点,放松,就是真正意义的生活。
三年的疫情,我开始对人的存在与“附近的消失”做深入思考。疫情的冲击让我对人类的虚无感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对人的生命有了更深的敬畏。生活和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逐渐将这些思考融入到我的工作内容中。新的一年,我的策展主题一如既往关注着人们细微的处境和情感,也会更加注重个体和“共生”这个概念。对我而言,时间早就不再是均匀介质,而是我的体验,我有意识地去体验文学中的时间、艺术中的时间、诗歌中的时间、自己当下体察的主观时间……试着去打破过去的思维惯性,以抵抗衰老和对时间的焦虑感。奢侈不是消费主义里定义的过分奢华,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感。这种奢侈可以是生命中的大段留白给艺术、阅读、跟朋友们漫无目的的交谈、放空自己等等。放松不仅是身体上的休息,更是精神上的松弛,自然而然呈现自己,流露真性情,这些体验可以带来更为持久和深层次的精神满足感。生活中有太多让我松弛和简单快乐的事情了,策展人这个身份意味着要解决问题,意味着责任,要付出很多,所以每次做策展都是要“下决心”的。如果不做艺术工作,那就做个轻松自在的读书人。
最后竟是两条杠给三年的疫情画上了句号,皆大欢喜又显得有点滑稽。在上海静默的两个月,辽阔变得珍贵,不想用励志故事来解压自己,只想在静止中手握自由,关注身边的事情。2022年我从架上绘画换成了架下装置,用手作的应答,表达新的思辩。今年又开始回到了架上,用刚刚结束的装置创作,作为下一个绘画系列的中转站。
时间是一条由自己去垂钓的委婉溪流,即使有愤怒也可以用一首诗慢慢舒展。人之所以有阅历,就是各种经验的累积,而经验本身没有好坏。艺术创作就是我的日常,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应该是额外的奖励了,希望今年有机会参与感兴趣的驻地项目。
“奢侈”更在于精神世界的表现,如果把一面湖的日出日落看成音符的升降,最后成了一首歌,是非常奢侈的,需要一颗真正自由的心。以前认为自由应该是财务、职业自由,甚至性别自由,但发现不够准确。如果是纯艺但无法维持生活独立,这不算自由;如果打卡上班还能副业做纯艺,未必是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
我希望的“放松”是不受外界干扰,不计较得失,不急于完美,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辨。过于恐惧批评和依赖赞美,或习惯于寻找懂,都是看不清自己的表现,那又如何能做到真正放松。
艺术家
“时间”这个标尺随着年纪增长反而变短了,大把用来浪费的时间现在开始斤斤计较起来。“用过的时间”也很宝贵,因为谁也不想拥有不好的回忆。而“未用的时间”意味着“计划”,我现在不怎么设定大目标了,基本上都是为自己设立一些阶段性的小任务,人越来越务实了。说大话谁都会,做计划最不需要下决心了,难的是兑现的过程。真正需要“下决心”的事,对我来说不免俗,就是与懒惰拖拉做斗争。在湿冷的雨天去工作室工作也是需要下决心的。疫情三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失去了最基本的出行自由。我开始反思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的真实性。虽然我的工作本身仍是围绕着工作室,表面上似乎和疫情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质已经不一样了。未来生活的琐事很多,新年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就是不要犹豫,凡事着手做就对了,最好还拥有处变不惊的“放松”,灵活、开放地去完成。生活就是艺术,任何工作做得好,都是艺术。
这三年,我变宅了,也开始学做饭了,生活变得很即兴,很多事儿就那么发生了。时间也是又快又慢,时间感变快,但又想放慢、放空,让节奏慢下来,到底是事儿急还是心急,这是个问题。自由自在是个很奢侈的事情,但如果不做艺术,也得做自己。
艺术家,策展人
疫情给我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应该也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不过不爱学习的人可能一无所获。疫情的状态就像是热气球遇到了阻力,可能是气流也可能是突然遭到一支飞箭。最主要的影响是让我更加珍视生命和时间,我意识到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时间是无价之宝。在这样的影响和认识下,我在新一年的工作中更加注重自己、团队成员、合作伙伴的健康,采取更加科学的工作和创作方式。
时间不仅是一种资源。时间的本质就是河流,它会带着也会带走我们的记忆和经历,疫情也被它最终带走。因而在我的工作中,我把时间理解为一种长情的生活方式。
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如果有的话,我想应该是参加艺术家驻留项目,在那里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专注于我的研究和创作。这个项目会令我离开我的家和家人,需要克服工作方式和文化上的障碍。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来邀请我,我很愿意去“下决心”。
“奢侈”就像一只蝴蝶。上个月我和艺术家何迟就在微信聊天中偶遇了这种奢侈。我们谈到蝴蝶的时候,他在中国,而我在泰国正恰巧偶遇一只蝴蝶。这种奢侈不是钱财或物质的堆积,而是对生命的感悟和享受。就在那个当下,我把蝴蝶的影像发给了何迟。
而说到放松,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放松就像重启电脑,人的内存和缓存都清空了,人清爽了。但是我愈发感到中国人很不放松,因为大家习惯了内卷。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选择做一些关注政治和环境的工作,比如从事智库研究或者可持续发展方面创新实践。
艺术评论人,专栏作者,策展人
“疫情”的致命性,并不在病毒而在“疫情”,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有一定的客观性,是一种单纯的科学,而后者的不确定性恰恰在于每个人内心的不纯洁。摘下口罩忘了隔离,如果不反思,没羞没臊,这三年的罪就白受了。病毒伴随着人类的成长,灾难一刻也不曾远离,明知道这才是常态,但人还是会忍不住悲观、神经质,或者说宿命感加剧。令我困惑的是教育的价值,很多高知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脑回路?!这一代人不做历史的绊脚石就已经是积德了。人到中年,我早就放弃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什么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很多事并不在个人或时代的掌控中,没心思搞那些虚张声势的语言游戏和骗人的把戏,在自己能把握的范围内做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就知足了。我可不想什么延退,我不想为艺术、为某某奋斗终身,我只想认真地为游手好闲而奋斗。一旦要下决心我就紧张,特别是做艺术工作,估计不做事就会放松下来。但人又不能生活在真空中,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游手好闲”是过分“奢侈”的。梦想是奢侈品、艺术是奢侈品,但艺术工作者不是。不过,梦想还是要有的,我在考虑回老家卖起重机,听说很赚钱的。去年春天我被隔离了三个多月,看着窗外的树发芽、花开、花谢,羡慕它们完整的一生中拥有那么多变化。我这样无知的人类,能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就很幸运了。
教师,画家
疫情三年对个人具体的影响不大,但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影响很大,仿佛很多东西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原来触及“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问题,总是一带而过,疫情三年看到的、听到的现实,感到梁漱溟先生思考的话题逼近自己,当然我们会用“等通知!”笑笑而过。你看时间停摆了,好像地球仍然再转,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急迫。最好不做太急的事情,放松一点,日常所有急迫与自己的获得有关,而这些获得的意义何在?从容是一种气度和修养,而要做到从容,就得从“不急”开始。画画也需要放松,这就和技术、认识有关。画画对我来说一直是业余的状态,我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如果不教了,我就去做艺术工作,如果艺术也不做,我就写作。中年人了,已经习惯日常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我倒是想下决心学开车,但下了十几年的决心,到现在还不会。
苏菲:重新找找老朋友
我的工作涉及国际文化交流与艺术出版行业交流,三年的疫情阻断了这个工作模式,也给心理上抹上了一层郁闷的浓雾。虽然从年初开始,贸易、经济上都有放开的迹象,但文化上的隔断和再次破冰会比其他行业要难许多。与前辈聊天,她指导我们可以尝试重新去找找老朋友,见过面的老朋友们,如重新为他们再做一个国内的展览,重新再为他们出一本新的艺术家书等等,开启较为单纯简单的第一步交流。我觉得非常好。
也留出了时间给予观察,在这个行为之下,有些人会慢慢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些人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我决定遵循内心的意愿去尊重时间和观察教会我的选择。
今年的工作计划,是将香蕉鱼书店“重新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文化交流、设计交流和行业交流,这三个方向是核心的理念。另外今年也是我们主办的UNFOLD上海艺术书展停办一年后的重新开启,今年的主题是具象诗,我们喜欢注入一点点新的知识量给到书展的展商和读者们,如花蕾般绽放,让大家各自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或多或少地,收获成果和想象。
如果不做目前的艺术工作,我会跟随近五六年的阅读方向继续深挖。如果有可能,再去美国或加拿大读个博士,之后再来想下一步可以做什么。
宋振熙:做一根挑事的“针”
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疫情三年,让我有了回归读书的机会。经历了这么一段奇幻的年代,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策展人的身份,当代艺术的本质,都有了更明确的自我认定。接下来的一年,我就是希望自己少谈“当代”,多做艺术。少固步自封,多破旧迎新。我有太多需要“下决心”的事了。因为有满脑子想要去做的事,都倒在了自身的精力还有“时间”杀手的面前,但这都好下“决心”。唯一难“下决心”的事是去做真批评的人,做真批判的行动,去说真诚的实话,做一根挑事的“针”,刺激下无聊又伪善的艺术现实。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就去街边做饭,或者守一家小店,养活自己,给别人填饱肚子。做一点踏实的事,或许更方便我们去理解世界的本质。“时间”是我现在活着的永恒对手,但也是唯一让我决心做艺术的鼓励者。不留下点超越它的东西,我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将都毫无意义。也要留点时间给自己,而不是被这个时代所拉扯和肢解。
石玩玩:去理解生命处境,还是为履历工作?
艺术家,教师
现在回头看,可能大家都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会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工作、生活、社交,更重要的撕裂了我们的共识。所以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疫情过后我们还能够以何种方式重建我们的共识?时间不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空间展开的前提,我相信现行的展览制度下,艺术家都有足够的理由重视空间,但只有将时间纳入空间的思考,这个空间才具有了延展性。下决心是基于意志做出的判断,如果是这样,艺术家的创造力其实就是不断地做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判断本身就是创造。在一个技术理性的时代,放松本身就挺奢侈的,我们都生活在规定好的盒子里,匆匆忙忙但又步履不前。我们需要占领一个又一个美术馆,完成一个又一个职业指标,想一想,我们是在理解生命处境,还是在为展览履历工作?放松一下,又如何?
策展人
疫情让工作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很多项目停滞或取消了。但更重要的是,还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折磨。生活在封控和极有限的开放之间摆荡,常常猝不及防地被禁足在家。漫长的三年,每天接收到各种荒诞和残酷的讯息,没人知道哪一天是终结。社交媒体上声嘶力竭的求救和质问投向无底深渊,到最后竟以共同等待感染来换取所谓的开放,但同时伴随着的还是无数重疾和死亡的消息。这一切留下的影响就是越来越深的不确定和无力的感觉。
新的一年注定只能用工作去摆脱这些影响。追回一点时间,平复些许情绪,尽管精神的创伤一定会一直埋在每个人的心里。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就变成了记事簿上的一件件事情。自己能下的决心,无非是争取让其中的每一项工作尽可能好地完成。回看某一个项目、某一篇文字没有白费时间,那才会放松,享受放松的时刻就是奢侈。艺术对我来说是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但也是一种缘分,同时还要靠它赚钱解决现实的需要。这是一份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工作,但是当现实需要没有这么重的时候,也许可以多一点旅行、阅读、电影,多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消磨时光。
艺术家
对我而言,疫情三年是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三年,以前的很多认知方式都要更新。这三年有艰难的地方,但得扛住,扛过去。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新的一年会慢慢恢复正轨,过去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也会在创作中显现出来。时间根本上来说是生命的幻觉,对生命来说时间是个沙漏,对生活来说时间应该是一条可以漫步的小路,而对工作来说时间是一张随时被刷爆的信用卡。工作必须要有效率,每天弹两个小时钢琴对我来说就是奢侈了。但效率是艺术的天敌,艺术是挥霍时间的浪荡子,接下来还是要下决心去做下一部动画片。如果不做艺术,我可能去做一个物理学家,或者就出家了。
毛文采:我已从50后熬成60后了
关于疫情的3年,我只想说我的记忆停留在2022年3月31日“禁足”之前的上海(此处省略5000字……),重启键始于2023年1月16日从浦东机场飞欧洲。经历“禁足”后的我,突然某日发现,3年——我已从50后熬成60后了!时间之于我已到了可以任意挥霍的年纪了!我应该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菜市场游荡,在纸质书里梦游,在黄昏里看日落,总之应该可以做很多浪费时间的事,对60后的我来说,可以肆意浪费时间就是最大的奢侈。我的工作计划也是我的人生计划,今年必须把公司交给年轻人,我已跟不上这个时代,但我有我的梦想要去实现!罗浮紫公共艺术就让年轻人去翻云覆雨吧!艺术是“毒药”,任何事都离不开她的魔爪,退休后,想实现的梦想也依然都与她有关!
艺术评论写作者
除去那些实际的影响,疫情三年更像是一场耗时漫长的耐受训练——让人更加直面表达的有限性,以及在有限范围内的言说,一种只能在直言和曲言之间迂回的言说方式。这三年对我工作的影响,或许就是它带来的创伤后遗症:必须重新调整对艺术表达的认知,并改变表达的方式。希望新的一年能够以此为基准,去调试着进行一些相关的艺术展示或者研究。时间还是一如既往,但“时间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形变,甚至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迫使人时刻去重新认知它。尤其是在工作中,人能获得的反馈,除了工钱,就是时间感——它的强度与长度,以及给予你的情绪与意义。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放松,也就无所谓放松了。但对于有工作要完成的人而言,与其说那是“放松”,不如说是“放风”。我有些排斥那些必须下定决心去做的工作。都到了不得不“下决心”的地步,那不论结果如何,往往都是不尽人意的。所以,但凡需要“下决心”,不如直接放弃吧。任何代价大于购买力,效用小于需求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奢侈的。如果哪天我不做艺术工作了,我就去当厨师、精神分析师,或者其他什么。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林薇:恢复口与腿的作用
疫情三年,让我突然开始正视“不确定”性,“不确定”带来的“变量”,变成了一种警觉。三年的时间,是这种警觉变成了一种短期的“急功近利”的急燥。在新的一年中,将不断提醒自己要放松下来,这种“放松”从身体开始,再到意识,跟努力不矛盾,类似于“冥想”中获得的体验,在平静中获得清醒,在解决身体的紧张里找到紧张的本质,或许这是一种“奢侈”。时间,总是无法控制地一天天流逝,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总担心自己被落下,不自觉中被信息的洪流席卷,总希望工作可以再快一点有结果。最近几年项飙提出了一个“附近的消失”的论断,流传很广。我理解是呼吁大家要恢复口与腿的作用,用口头传播、亲身参与的方式,来抵销电子媒介造成的文明危机。疫情三年,也在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当下亲身地体验它,这就好比两块明亮的镜子彼此反照一样,我们从生活中总能“看到”自己。我们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指示来体验自己的生活,而只能靠着我们自己来亲身感受生活的苦乐。新的一年到了,阴霾似乎散去,如果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都可以看成是人的延伸,我为自己一直从事艺术工作感到欣慰,可也时刻提醒自己:“艺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要警惕艺术里“延伸迁移”的发生。我想,不做艺术工作的时候,或许可以做一位“口传身授”的禅修者。
梁庆:我想继续保持陈旧与缓慢
策展人,出版人
疫情三年减少了远程出行,让我得以充分感受自己朝夕相处的城市,因此新的一年会做更多与之相关的项目。随着年岁增长,时间于我而言越发意味着选择:选择和能有共感的人、事、物相处,时间才体现价值。现如今节奏太快,而我想继续保持陈旧与缓慢。面对爆炸的讯息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我更喜欢往回看,在已经发生或做过的事情中,还留存着感受和可能。所有的工作都须全力以赴,要“下决心”的往往是如何结束一件工作,那代表做事的标准和态度,也意味着能否有新的开始。奢侈是灵感能不断冒出,放松是能在大街上愉快散步。不做艺术工作?不可能,生活全部都是艺术。
艺术家
疫情这三年对我影响还挺大的,方方面面,感情、工作、生活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外表来看我应该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但我好像总是会跟“过去”过不去。2009年我有一件作品的名字是“我们生存的立足点除了不断消逝的现实之外,别无其他”,这句话是叔本华写的,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现在觉得确实挺有道理的,人应该向前看。我越来越能感知到年岁的增长,而且就增长在自己的身上。我没有什么爱好,也不太会放松,艺术就是全部了,工作上没有什么需要“下决心”的,很早就下过决心了。未来的生活计划倒是给自己下了决心,世界这么大,我想多看看。我的生活好像一直都不安分,也没乡愁,人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李青:切勿躬身而入任何不可掌控的局面
艺术家
时间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用来感受和度过的,然而记忆事后会做出它的选择,就我而言,工作中的细节常常比生活中记得更为真切。纳博科夫一定能把对蝴蝶翅膀的记忆建成一座宫殿,认知决定了记忆的容量。艺术家的作品也是记忆的宫殿。在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去做,这是一种“奢侈”;在你做不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去做,这是一种“放松”。另一种“放松”是做了唯你能做的事情并专注于此,有幸之人才可以达到这种“放松”。如果不做艺术工作,也许我也会去研究自然。疫情三年终于过去了,要说和以前有什么大的不同,可能是更多地目睹了友人之间的共情感喟,屈而不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个人在自然面前,和在现实面前的双重无力,无法不让人加倍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能掌控的东西不过寥寥。以后在现实事务面前躲进小楼,切勿躬身而入任何不可掌控的局面和场面,也许是一种选择,做减法可能更需决心。
策展人
疫情三年,戛然而止。在开始与结束之时,方能感受离情。将近四十不惑的年纪,预示着世事难得糊涂!回不去的时间,回不去的空间。其实,不惑也惑,糊涂并非糊涂。小时候,老家有个算命先生叫“潘瞎子”,说我命在北方。时过境迁,夜泊钱塘。有些年不算命,也不信命了……“时间”就是面对现实的不妥协。小时候,梦见自己在长大后的画室。多年后的梦境重合,恍惚预见前世。彼时梦杂糅,就连春梦也少了。与此相较,内卷与躺平互殴,如今又生发“与生活讲和”的假象。真相是奢侈的,除此之外皆为虚幻。但我决心做个问心无愧的人,也不断对自己进行忠告——治好学问,才有说话的资本。“下决心”是心理与行动博弈后的战利品,说不清好与坏。做艺术工作就是在建构自己的精神谱系,艺术只有作为抵抗形式才有意义,要朝向阳光,而不是做只黑夜里酣睡的猫。
51%的艺术从业者
我现在好像变得不那么愤怒了,经历了这三年,好像被打败了,开始考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但是又有点不甘心,有点没骨气了。有点害怕去想“时间”的问题,想时间过得快一点,这样好像一切都会好起来。也有点急促了,想让时间变现。
感觉只要是工作都是需要下决心去做,如果有得选,谁会愿意做“工作”呢。奢侈是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且不会饿死。什么都不用想,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很放松,或者单纯晒个太阳喝杯咖啡。
不做艺术相关的工作的话,依然最想开个小店,一个很晚开门,开到深夜的店。
艺术家,策展人
“时间”就是内心的尺度,是生命的节律和工作的暴政之间的谈判和博弈。心态好的话,花几周刷一部长剧也是值得;心态崩的话,陪父母陪孩子都是焦虑。放松一点,放弃人设,活得真实,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会犯错的,需要别人帮助的。明白一篇文章或一个展览都没有那么重要,也没那么不重要,不必期待过多,也无需担心后果,只管如实地说,勇敢地做。疫情三年让我感到很多东西停下也挺好的,社会未必需要这么多的新闻,艺术也未必需要这么多的展览。多读点书,多陪家人,无关痛痒的事儿可以少做。没有年度工作计划,走一步算一步,等工作找上我。能力够不上欲望,执意追求,就太奢侈。真奢侈了一把,得到的也吃不进去,只是高价进场,坐在台下,看完一场虚荣心的表演。不做艺术工作的话,做社工。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去社区当老师,当义工,发传单,只要在社会上散发热量,都会感觉不错。当然,这是反应性的答案,因为艺术工作有时让人疲倦,似乎还离真善美和日常生活越来越远。
艺术家
三年的疫情带给我们的是太多的不确定性,所有的计划都在变化中消失了。非常态变成了常态,以至于来到工作室打开电脑,会想很久自己的东西放在哪儿,走到外面甚至感觉太阳太亮,过于刺眼。
终于开放了,却还是谁也躲不过“阳”,折腾了好一阵还是觉得虚弱不堪。至于新一年的工作。就像昏沉懵逼中迫切需要考虑的一样,把没理清的思绪好好地理一理,先把前两年没干完的想办法实现了吧,好在一切似乎都在欣欣向荣起来了。感觉地球似乎转得比以前快了,不知不觉中时间就像水在指缝中溜走了一样。但有时又觉得反正也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溜就溜了吧,不断原谅自己,因此常常处在躺平和焦虑的矛盾状态中生活和工作着。我们天天努力地做作品,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但艺术的信仰没变。能够不用含蓄,不用伪装,直接了当地面对生活和工作,这就很奢侈了。
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写作者
交往空间受限,人事范围缩小,外界吸引力变弱,这是疫情三年带来的影响。倒是在自我意识上轨道,经常想做帕斯卡说的“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要学会选择,对人,对事,对物的选择。好比一个下午的阅读时间,我要先从书架上作出选择,这个下午的意义,就在于我为它选择的内容。对于工作,我有“狮象搏兔,皆用全力”的毛病。只觉得尽兴而为才能畅快释怀,所以,单纯是事事都有决心,累,要改。但新的一年还是要集中注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生活已经离不开艺术了,如果真的不做艺术,也许当个家庭主妇也不错,发挥想象力和创作性的机会多一些,对于母亲这一角色而言,很重要。无所顾虑,尽兴而为,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成人世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艺术家组合
我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一直挺和谐的,并不需要去下什么决心,即使不做艺术工作,也会继续和公司团队的伙伴们一起,做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做的事情。“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自己的生命所安放的地方,能够拥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就已经很奢侈了。这三年看到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让我觉得有必要在新的开始之前,对很多人、很多事物的理解进行比较大规模的修整,假如采用“人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定义(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可能就要从修整自己的社会关系出发。
疫情三年的影响还是重大的,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我这个年龄与职业来说,影响是显见的。至少让你再次感悟,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什么也不是那么简单。至于你的个体立场如何体现,这需要智慧。我没有想过新一年该怎么开始或者重启,对我来说,生活与艺术工作其实都在惯性与判断中维系着、推进着。时间总是被生活与工作分配、消耗。当然每个人的时间意识和态度是不一样的,时间有它的恒常轨迹,不会因为我们的意愿而留情。“时间”在我的生活和艺术工作中,可能只是希望在庸常的日子里,把握一些时刻并激活那个时刻。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包括艺术,不是说你下决心就可以解决和做到的,得靠机缘与心智。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决心与主观意愿、能力能够一致,或许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否则可能成为难为自己的事情。我的工作计划多半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如果说暗暗下过什么决心,那就是希望在这个时代与社会中,能把自己完整起来,以真面目为人处世,自然而然,不苟且、不做作。今天的一切都很难,潮流、功名、欲望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趣味。能够有自由的思想空间与心性一致的行为,不为欲望、潮流所动,已是奢侈。作品的建构其实也是一种完善自己的道程,如果不做艺术工作,但至少会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芬雷:不合时宜的出行
艺术与出版策划人,方志小说联合发起人
防疫更紧张的两年,几乎都在路上,绝非刻意,却难得经历了不合时宜的出行。所谓“下决心”,不是在“三年”后的今年,而是在2021年。决心之事,跟我一直在参与的“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有关。2020,驻地计划停了一年,到了2021年,我决心将当年驻地计划的地方全部去一遍。到地方上去,有两个考虑:一是确实惭愧,此前因为杂务缠身,每年的驻地只能去两三个地方,愧疚于联合驻地中每个地方的组织策划者以及驻地作者,要求自己务必全力去沟通和协调。二是因为疫情,想要了解地方到底在发生怎样变化,我们究竟置身怎样的现实处境,让自己的视野暂时离开书本、屏幕和熟悉的社交圈。2021年和2022年,先后去了至少25个市镇,如果算上村庄,可能接近50个。感触不可谓不深:在顺德,第一次知道淡水鱼塘养殖海鱼需要进行人工海水改造。在漳州一个九龙江边的县城,光水电站水坝据说就有200多座。在淳安的浪川县,去年夏天的持续高温,让耐高温的蚕种大面积发病,茧站技术人员不经意间关于养蚕发病所说观点,竟然和费孝通《江村经济》中80多年前的一段话完全吻合……这些不合时宜的出行,让我对地方和驻地计划有了新的认识,就像社会文化人类学强调的,“小地方,大论题”,看似偏僻的地方,却可能链接着全球的论题。一个想法,从去年到今年,仍在推进:方志小说在游牧式驻地的同时,值得尝试在某些地方落脚,以“方志小说工作栈”的形式,将驻地、研学、展览、活动等嵌合在一个实地空间里,围绕地方上的事情展开更为深入也更为长效的工作,仍然从艺术和多学科的驻地出发,保持与本地实践者以及本地组织和机构的互动,进而推动地方共益。这会是今年尤为重要的一个计划。
戴建勇:多思考少行动
艺术家,麻痹公司主理人
2022年上海疫情开始,我们全家到了海南万宁,虽然避开了上海最痛苦的3个月,但整个人都很紧张,因为上海的家里有宠物和老人。解封后整个人相对放松一些,可以面对山海天空云朵,反思生命的意义,“自由”是奢侈的。疫情三年,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一切的不确定性,让人变得麻木了。时间已经给我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比如眼睛老花了,开始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的作品一直和时间有紧密的关系,《朱凤娟》我已经拍了14年了。我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到175cm了,这就是时间。2023年也挺奇特,二月就有了很多艺术展览,因为很多艺术家疫情的时候都在创作。我的这一年要慢一点来适应这么快的节奏,多思考少行动。我不做艺术的话就去支教,真正好的教育让人一生受益,而坏的教育影响的不止是一代人。
艺术家
“时间”是最值得用个人方式去“浪费”的一种东西。在这魔幻的三年,现实和艺术似乎有了更多对流的缺口,我把自己当成道具去尝试一些“出格”的事情,过程很辛苦,但也很精彩。
今年呢,道具和我似乎可以合体了,好多有趣的念头都在脑海里盘旋。我如果不做艺术工作了,我就去做个专职父亲。不过动动嘴巴就能搞定的事情都是奢侈的,我是一个纠结的行动主义者,好多事都得默默下决心。
陈娅:更好的世界不会凭空降临
策展人,江苏省美术馆展览策划与研究部副主任
疫情三年,等于时间浪费了三年。当不久前发现自己的工作环境已经在审查中主动规避曾视作如椽之笔的“抗疫题材”时,内心生成了一种混合着愤怒、无力以及偷着乐的复杂情绪,而现在回想起这个情绪竟然就是自己三年来的总结。没有人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治愈三年的群体PTSD,但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更能让人看清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社群的复杂性。所有个体都可能成为弱者,而所有弱者都共有同一种命运。我们需要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不停地在好奇和怀疑之间寻求平衡,才能在数据的洪流中明辨信号与噪声——不以立场划分善恶,是当代人的奢侈品格。
工作和生活一样,下定决心践行的都是一种更积极的多样性关系,突破盲点和同温层的关键是将跨领域的信息集合起来,重建一个可容纳更多差异性的空间。今年的展览项目也是希望做出这样的实践,把不曾描述过的故事言说一遍,把不同行业间的思考连成一片,把这三年失去的时间寻回一点。但通过信息碎片构建的也只是知识状态的表征,而不是客观世界的表征。
更好的世界不会被给予,不会凭空降临。虽然我希望2023能是好的一年,但面对不一定会变好的世界,我们唯一可能的迎接它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强。如果不做艺术工作大概会去讲脱口秀吧,不过这好像也是一种艺术工作……
陈荣辉:作为世界公民
艺术家
这三年的经历是充满了戏剧性,去耶鲁大学读了MFA,顺带有了娃,做了三次个展,都没有办法去现场参加开幕式。三年时间往返中美,一共隔离了3个多月,中间还去新加坡待了14天“洗白”,还去德国转机。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经历,反而激励了我作为世界公民的某种特质。接下来的创作依然是在全球化这个背景的下一些视觉探索,听起来有些土,不过是我真实感受到的东西,坚信所坚信的事情。
经常会听到摄影师或者评论家说,摄影是关于“时间”的艺术,我其实不是很赞同。对于静态图片来说,时间是个伪命题,图片里面的时间无法流动,但是这种凝固的瞬间是有趣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年龄大了,只是看到自己的娃瞬间长大了,只有在陪伴的时候才意识到时间的飞逝。
工作上每一个项目做起来都是需要下决心的,特别是实际“上手操作”的那部分,一定要找理由去逼迫自己动手,动身子,然后项目就开始运转了。如果不做艺术的话,我应该会去做房产销售,买卖房子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
曹恺:打造一个旧媒体实验室
当代艺术与电影的实践者和研究者
大疫三年,一个共识是,这将成为一个用以断代的时间坐标。对我而言也是如此,譬如“须发渐白”——说是“渐”,其实是某种突变。2020年初封控在家时自拍,突见一根雪白的鼻毛龇出,立拔之;某日刮脸,又见下颌胡须忽然染白半边;未几,理发时观镜,两鬓亦开始斑驳。去年曾集旧唐人句,曰:“燕山雪花大如席,两鬓白如雪”。2023年,大疫三年翻篇后的第一年,是重启之年,某些中断的、延缓的计划将再度发动、加速、运行。打造一个“旧媒体实验室”,是既往三年中持续推进的一个实体建设。本意是对古典录像艺术的媒介抢救,事实上,创制一种影像文物再度进入数字传媒的机制;作为一台某种意义上的“时间机器”,因为物流停滞而一再延缓了实验室的总配时间,尤其是关键的“模拟/数字”多进程转换模块,一直到2022年末才获得解决方案。当然,我也一直在“下决心”寻回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这需要重启腐烂在硬盘中许久的一些艺术生产计划。我从未想象过我会离开艺术,但是,如果艺术真的有一天要离开我,我该如何来填补这一缺失呢?我为自己假设了三个可选的非艺术身份:乡村教师;野外考古工作者;私厨主理兼大司务。这三个身份其实早已具备某种隐匿基因,需要的只是激活条件而已。
毕蓉蓉:缓一缓
艺术家
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变得越来越“多”了,就是我更能扎实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三年对我来说很特别,一方面是防疫,一方面要养育自己刚刚诞生的宝宝。疫情前的2019年,我处于一种非常忙碌的状态,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展览,不停地创作新作品,也结识不少良师益友。但同时,我也在提醒自己,需要缓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因此疫情之下各种展览节奏的放缓,加上宝宝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自我调整,这种调整,让我拥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去准备2022年底的个展。当个展作品呈现出来时,我觉得它们和之前的作品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接下来,还是需要进一步地根据环境和内心的变化去展开新的工作。艺术家的好处就是一直在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路途中,我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
btr:我就像快要干涸的植物
写作者,译者
疫情三年,行动受限,视野变窄,但也变得更加关注周围。比如上海那些本不常去的街区,附近的街坊、楼里邻居,甚至在小区里仍贴着世博会宣传牌的破败花园,我也能玩得津津有味。我现在就像快要干涸的植物,新年里要去贪婪地汲取一些外部世界的养分。时间像一种制造弹性的催化剂,每当时间紧迫,反而会有更多灵感和生产力。没有需要下决心做的事,多数是因为热爱或事情本身的愉悦而去做。对我来说,专注而紧张地做一件事情,其实是放松的,如果不做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想做一个“专属聊天机器人”:当人们以为在和机器人聊天时,我是那个躲在机器背后的人脑——那样或许会更了解人类吧!
Ag:回撤,卸除,再炼
写作者
疫情其实给我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它将无常这个东西推到脸前,这个距离近到你根本无法回避或视而不见事情的本来面目。它提供给我一个可能有点极端的机会去回撤、看、卸除生活中不真实的部分吧,然后情绪回收,废物再炼,同时也学会更加共情。
时间对我来说是某种和死亡有关的感觉,它只是一种感觉,很主观,具有相对性。当代生活里时间不够用,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外在的各种技术媒介消耗的,但其实是被我们的注意力和欲望内耗导致的感觉。除了死亡,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游戏,或一个梦中闹铃,或一团纠缠在一起但并不存在的面条。
“下决心”这个词有点重,有时候只是在一个境遇的当下知道要这么做吧。就个人今年更具体来说,是完成一部影片和一本故事书。但我经常计划跟不上变化。我并不觉得我是从事艺术工作的……那是被大多人定义的。其他工种倒是都可以尝试,有些也确实做过。活着本身就是一项总体的工作了,只是它会按照每个人的情况不断地分形。很多人觉得在山洞里闭关的那些人不是在工作,这是错误的见解。
“奢侈”可能就是用我们这个有着无限潜力的心智却不断去重复ChatGPT能做的事,关于知识的物质主义,既自我肿大又自我阉割,这是奢侈的。而“放松”就是显现真实本性。
aaajiao:从快速逆行的车上跳下来
艺术家
很多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其实都和作品无关,倒是需要下决心去进行一些社交。这三年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从快速逆行的车上跳下来,回头发现这辆车掉头了,我决定自己走向我的目的地。可以徒步前行或者后退,既没有饿死,也没有被豺狼虎豹吃掉,我觉得这就很奢侈了。
创作曾经是挽救自我的方式,现在是在生活的日常中,通过做作品让自己保持好奇心。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奢侈放松地活着。
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artdbl2017,电话:0755-86549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