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 0
- 0
分享
- 《戏剧》2022年第3期丨吴靖青:约恩·福瑟剧作中的音乐性
-
原创 2022-08-12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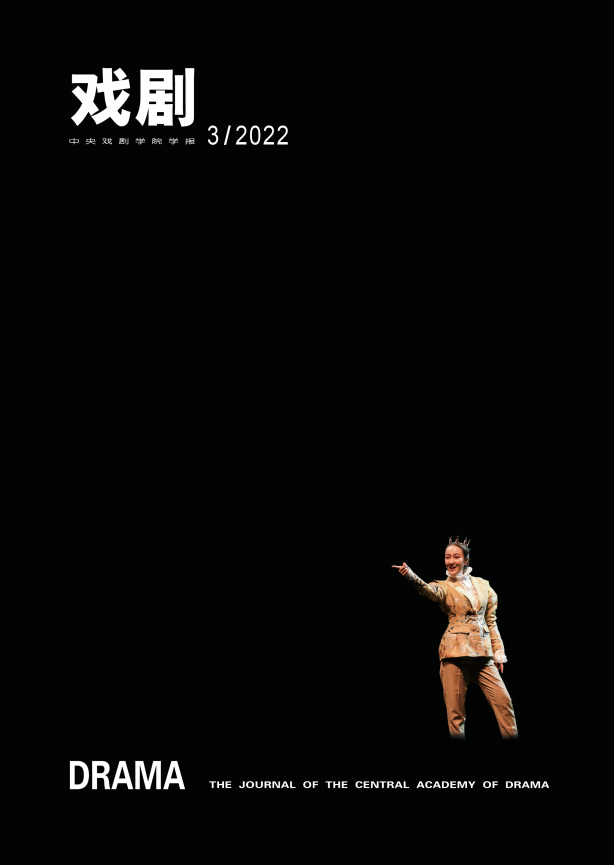
约恩·福瑟剧作中的音乐性
吴靖青
上海戏剧学院期刊中心《戏剧艺术》责任编辑,研究员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北欧当代剧作家约恩·福瑟因全面开掘剧作的音乐性而独树一帜。他将节奏化和变奏效果贯彻戏剧语式的始终;他注重戏剧音乐性的时空开掘,在凸显“戏剧复调”的矛盾性张力的同时,又全力打造“戏剧复调”的整体统一性;他注重音乐性对全剧的定调与“数理—艺术”作用,为“极境”注入细腻感与丰富性,达到了抽象与具体、“极简”与“丰富”的精妙平衡。
As a contemporary Nordic playwright, Jon Fosse makes a great achievement in delving into musicality of drama and develops a school of his own. In the respect of dramatic language mode, he sticks to rhythm and variations. He also puts emphasis on time and space, foregrounding both the tension and integrality of the dramatic polyphony. He stresses musicality’s tone-setting and “mathematics & arts” effect in playwriting. His works boast delicacy and richness and keeps a subtle balance between abstract and concrete as well as simplicity and richness.
关键词丨Keywords
福瑟 剧作 音乐性
Jon Fosse, playwriting, musicality
北欧当代剧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其作品“早已无远弗届,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1](P1)“初读他的作品,最醒目的特点之一或许是徘徊其中荒诞派的影子—品特似的重复与静场,以及向贝克特致敬的主题。这也是人们称他为‘新品特’和‘新贝克特’的原因。”[2](P6)话说回来,尽管福瑟常被拿来与贝克特、品特相类比,但其作品仍具有显著的专属于福瑟本人的风格。这种独特性源于福瑟对其剧作中音乐性的全面开掘:他将节奏化和变奏效果贯彻戏剧语式的始终;他注重戏剧音乐性的时空开掘,在凸显“戏剧复调”的矛盾性张力的同时,又全力打造“戏剧复调”的整体统一性;他注重音乐性对全剧的定调与“数理—艺术”作用,为极境中的舞台事件、人物关系、人物行为注入细腻感与丰富性,达到了抽象与具体、“极简”与“丰富”的精妙平衡。
福瑟在从事戏剧创作之前曾是流行音乐乐队的一员,音乐艺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戏剧创作。他的剧作大多既非歌剧又非音乐剧,而是一般概念下的“话剧”,但包含着某些显著的音乐要素,集中体现了某些音乐的美学规律,具有突出的“音乐性”。由于人类审美心理的整一性、通感功能、“共感知性”,“音乐性”在不同艺术门类中有多种跨界的解释,比如,诗歌的音乐性节奏被称为“韵律”,甚至一些绘画中也有“旋律配合、和声、变调、调性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3](P123)福瑟的剧作致力于戏剧的音乐性,恰恰说明他在戏剧创作时全方位地动用了审美心理的综合要素,也恰恰说明他的剧作有明确的目的—用于演出甚至便于演出。
一、戏剧音乐性的语式开掘:节奏化和变奏效果
节奏是音乐的基本要素之一,福瑟对戏剧音乐性的开掘首先体现在台词的全面节奏化上,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对戏剧语式的全盘节奏化控制。“比起古典戏剧来,现代戏剧更加借助于语式并就语式做文章。”[4](P225)“他(福瑟)的笔下滋生出一种独特的情绪与氛围,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太多的话并未宣之于口。同样,也有太多的话不断往复迂回。对话中断继而接续,仿如一列缓慢逶迤而行的慢车。”[1](P2)这些台词全都像歌词或诗歌一样分行,行末不打标点符号,只通过分行来显示节奏与起承转合,并且经常在重复中出现变化,在变化中出现重复,这些独特的语式呈现了人物语言、行为的多次停顿、承续、转折、往复、游移,从而折射了人物复杂的思想情感。“语式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内容本身:所说的并非疑问或疑惑的对象,而更多是这种疑问或疑惑本身,制约着某种与对话者的语言关系的类型。”[4](PP224-225)
对于现代“非音乐剧”或“非歌剧”的戏剧台词的节奏化,贝克特和品特在福瑟之前就做过大量的探索,因为他们意识到艺术形式能成全艺术本身。贝克特说,“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与凌乱相宜的形式”[5](P74),“‘别绝望,其中一个小偷得到了救赎;别假设,另一个小偷下了地狱’那句话有精妙的形式,是形式成全了它”[5](P79)。关于语式节奏化,“在贝克特的《最后一局》里,人们可以从第一句句子看出语式如何被安排进去;‘完了,已经完了,快要完了,也许就要完了’”。[4](P225)此外,贝克特的一些台词和对话还在语式的节奏变化中推动剧中两人的性格—大前提一致下的小龃龉:
爱斯特拉冈:看不见垂枝。
弗拉季米尔: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斯特拉冈:看上去简直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丛林。
爱斯特拉冈:像灌木。[6](PP628-629)
比起贝克特,福瑟对语式节奏化的铺展是尤为彻底的,如同音乐,从主题到装饰音等旋律的变化,全都纳入了节奏(或节拍)的轨道。在福瑟的《而我们将永不分离》中,一个四十岁的孤独女人无时无刻不盼望“他”回家,但这种盼望中掺杂了太多的失望、怀疑和自欺欺人,她一面说“我一个人过不下去”,一面又说“我坚强伟大又聪明/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7](P31)重要的是,这种复杂的思想情感通过节奏反复出现,带动全剧的音乐式主题,“而且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但我不是孤单一人/我从来没有孤单一人过/我一直都只有孤单一人/我从来就没有不孤单一人过”[7](PP5-6),“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我知道他会回来的/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我在等待着他/可他已经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7](PP13-14)。《死亡变奏曲》中那个曾经充当了“女儿”的心灵慰藉、又不幸成为她的死亡召唤者的男性“朋友”,他的台词总是跨越了肯定和否定,他对生与死、短暂与永恒等事物的作用与意义反复体现在音乐式的“对立之言”中。“我们始终都站在那儿/而我们又从未站在那儿/那是多么美好/又多么痛苦”[8](P448),“一切都早已消逝/而一切又都刚刚发生”[8](P448),“我将永远不再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8](P451)。肯定、否定、双重否定等句子的参差变化在语式形态上纳入了节奏的轨道,在意义上不断通过制造“逻辑矛盾”来揭示人物的心理矛盾,甚至以此构建戏剧舞台事件的基本矛盾。
这些剧中的个人独白就这样在曲折的节奏和韵律中自相矛盾,而节奏化对白所呈现的角色之间的矛盾与龃龉也俯拾皆是。《有人将至》中的“他”和“她”在“没有人会来”和“有人会来”之间发展节奏及人物矛盾。在另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前,“他”心绪平和,觉得“没有人会来”,而“她”时有隐忧,觉得“有人在这里/有人会来的”;在那个“男人”出现并与“她”交谈后,“她”解除了隐忧并小有期待,而“他”在抑郁和恐慌后居然“十分冷静地”说出“我早就知道/有人会来的”。[8](P189)“他”后来的这种“冷静的愤懑”令人联想起爱德华·蒙克的油画《妒忌》—妒火事实上已经燃起。然而还需注意的是,矛盾性中仍掺杂着“一致性”,这往往是剧中发生矛盾的两人仍能共居一室的前提,但这又继续引发新的矛盾。比如,《名字》中没有养家糊口能力的“贝厄媞新男友”在贝厄媞怀上他的孩子后,与贝厄媞一道寄居在贝厄媞父母家。他与贝厄媞的语言节奏有顺接性和一致性,如“我们在这儿不受欢迎”“我们还能去哪儿呢?”的诗歌化对白与重复,否则他就会直接与贝厄媞分道扬镳。[8](PP72-73)然而,共居一屋又带来新的矛盾。内向、焦虑的他私下里对贝厄媞发出深邃的生命感言,“没有出生的孩子当然也是人/就像死去的人也是人一样”[8](P72),这引起了贝厄媞的伤心和反感。这些剧中大大小小的矛盾与龃龉,由于贯穿全剧的节奏化处理而连缀成音乐性的组织。
戏剧节奏化手法中,“重复”或“有变化的重复”语式起着重要作用,而戏剧中有变化的重复语式就对应着音乐性中的“变奏效果”。在福瑟之前,品特也精于此道。品特独幕剧《微痛》中“被重复单词中所具有的连续性”,“第一个在紧张和停顿中结束的渐进,通过第二个渐进得到了反映”,“第二个单元或戏剧构造吸引了第一个重复,并将其加以发挥”。[9](PP36-37)“品特通过强化重复”而揭示人物情感关系,在独幕剧《微痛》中,“爱德华和弗劳拉的世界是风雨飘摇的”[9](P38),“语调变化了好几次,但龃龉来自威胁性的氛围”[9](P212)。与品特相比,福瑟更追求台词节奏化、重复语式的极致效应。从更确切的角度说,福瑟剧作台词的“重复”不是“复制”,而是“变化的重复”,它系统地、大量地、首尾呼应地出现在福瑟剧作中,使这些剧作某种程度上成了“变奏曲”。“变奏原则建立在不变的因素与变化更换的因素同时结合上。不变的因素使我们辨认出反复出现的同一的原始主题—旋律,而变化更换的因素使原始主题—旋律不断出现新面貌和表情素质。”[10](P419)《有人将至》中,在另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前,“他”所说的“没有人会来”与“她”所说的“有人在这里/有人会来的”,当这几句对话保持基本句式不变时,随着主人公语气的细微变化,呈现出几分“固定基础变奏”效果;当这几句话前后又添加了大量辅助性、修饰性语句时,主人公思想与情感的表达变得更为丰富流畅,类似于“变体主题变奏”中的“装饰变奏”。随着剧情的发展,在陌生“男人”出现并与“她”短暂交谈后,“他”一反常态,语气、性格发生“大裂变”,愤怒而讥讽地、有变化地重复起“她”开始时说的话,“我早就知道/有人会来的”,这又类似于“变体主题变奏”中的“性格变奏”。同理,《一个夏日》《而我们将永不分离》等剧作中,在女主人公等待的过程中,由疑虑、彷徨,到愤懑或感伤,往往伴随语式的多种类型的变奏。
二、戏剧音乐性的时空开掘:“复调”及其对立统一
福瑟对戏剧“音乐性”的开掘还体现在“复调”的大量运用上。在福瑟之前,贝克特常在剧作中嵌入“复调”并使之相互渗透。贝克特的剧作“缺乏情节”,“它们不是以单一的线性方式发展的,它们从本质上说是复调(polyphonic)的”,“这些复调综合各种陈述和意向,形成某种组织结构,相互交织,须从整体上进行理解”。[11](P45)贝克特已为“戏剧复调”作出贡献,而福瑟更是让“复调”无孔不入地充盈戏剧的全身。
“复调”这个本身来自音乐的名词被巴赫金隆重地运用在“复调小说”的阐释上,复调理论在音乐以外的艺术领域被广泛借鉴,巴赫金功不可没。尽管复调小说并不是戏剧,但复调小说同那些“非复调小说”比起来,离戏剧的距离显然更为接近。复调小说舍弃了第三人称,“要求把小说结构的一切因素全盘对白化”[12](P105),作者“必须有很高的、极度紧张的对话积极性”[12](P110),而这正是众多戏剧的根本特点—因为许多戏剧都强调演员间“对话”和“舞台交流”的积极性,以及“授”与“受”的你来我往。复调小说中,“一个人的内心矛盾和内心发展阶段,他也在空间里加以戏剧化了,让作品主人公同自己的替身人,同鬼魂,同自己的alter ego(另一个‘我’),同自己的漫画相交谈”。[12](P60)复调小说的上述特质,在戏剧(尤其是现代戏剧)中可谓不胜枚举。此外,复调小说中,“这一(对话)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这种对话(整部小说构成的‘大型对话’),并非发生在过去,而是在当前,也即在创作过程的现在时里”。[12](P103)如果从“创作过程的现在时”的角度看,戏剧就是天然的即时性艺术,无论是对过去的回忆还是对未来的幻想,无论是叙事体戏剧还是非叙事体戏剧,事实上都需要舞台的现场呈现。可见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基础与戏剧艺术规律并无本质冲突。
福瑟剧作中“复调”的独特性在于,这种类似于音乐曲式的组织形式自然而然、淋漓尽致地出现在他的戏剧中,不仅大概率地出现在对话中,而且极贴合地出现在舞台动作中。“(戏剧)复调话语的最初形式无限地有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人物与自身的不一致性、对人物整一律提出了疑问并在其话语中揭示了所出现的历史矛盾远在于个体心理之外。”[4](P234)《我是风》的演出介绍上说,“两个人,又或许只是一个人分裂成两个人”,这显示出角色分裂后形成了戏剧复调。剧中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乘一只小船在海上航行。在航行中,“一个人”在犹豫中保持着固执,要驶向外海,而“另一个人”总是在质疑“一个人”,发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的暗示或指示。他们的复调式对话,可视为“一个人”身上分裂出的“另一个人”与“一个人”身上深不可测、不可救药的自己形成了持续的矛盾,而结局是“一个人”终于摆脱了“另一个人”,使自己消失在风中。直至结尾,这两个人之间的台词和舞台行动(包括静场)都有很强的“复调”意味:
一个人:此刻我被带走了(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人:我只是就这样做了
另一个人:可是你害怕这样做
一个人:我是如此的害怕/正因为如此我就这样做了/我知道我会这样做的(短暂静场。)/我太沉重了(极短暂的静场。)/而大海太轻盈了/风太急了[7](P457)
还需要注意的是,从形态的复杂性而言,戏剧复调超越了巴赫金复调小说中的“复调”,与复调音乐中的“复调”更为接近。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力图将不同的阶段看做是同时的进程,把不同阶段按戏剧方式加以对比映照,却不把它们延伸为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复调小说“主要在空间的存在里,而不是在时间的流程中”,“是否能同时共处,是否能并排平列或分立对峙”是复调小说的标准。[12](PP59-60)在这一点上,戏剧及音乐与复调小说不同,戏剧及音乐的场域总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缺一不可的参与,戏剧中的人物即使在并排平列、分立对峙或呈现某一时刻的剖面上的相互关系时,仍然不能失去时间流程这一维度。在时间这一维度上,戏剧同音乐一样,与某些视“语言”为“事件”的现代语言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语言一段时间后恐怕不再同先前一样”,“这是因为变动是与单独的事件相关的,尽管变动在空间上是不同的。时间,即便缩小到空间上的一个点,也将产生变动。相反,空间若没有时间,就无法产生任何变动”。[13](P268)因此,福瑟的戏剧复调即使在所谓“共时并置”的空间里也仍然强调对话、舞台动作的时间性和流动感。
《死亡奏鸣曲》颇类似于复调音乐对时间与空间的交织性依赖,尤其是最后部分出现了“年老女人”“年轻男人”“年轻女人”“朋友”“年老男人”“女儿”六个角色共同在舞台大框架上的对比映照。他们有着各自完整的“小宇宙”(有时他们中的两人或三人还能形成“小宇宙组合”),但他们并不全然如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那样“星散在一个广阔平原上”[12](P59),因为他们带有各自的“时光流动和时光倒错”的功能,由此才带来了大大小小的舞台事件与舞台动作过程的交错、衔接与因果关系。尽管这些事件总体说来共处于最后一幕的舞台空间上,但时间并没有真的凝固成一个点。在结尾处,“年老女人”悲叹“女儿”被人发现“漂在海上”;“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即“年老男人”和“年老女人”年轻时的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为自己神秘的“不再回来”和“再回来”发出警示;“年老男人”对“年老女人”采取了决绝态度;出现了一段较长的“女儿”的台词,她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循着召唤(某种程度上来自她对“朋友”的理想化认识)走入大海的波涛中(福瑟特意在剧本中强调“女儿”这段话是“自远方说”,体现出流动的时间里舞台空间的“并置”);接着又出现“年老女人”和“年老男人”恩爱尽失、难以相互面对的情形;最后是“女儿”入海后无法弥补的后悔,“我后悔了/我想回来/我想再次独自一人/我不应该”。[8](PP450-453)毕竟,戏剧(尤其是戏剧演出)中的“复调”是时空交织的,这与音乐织体(包括多声织体中的复调音乐)对时间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双重倚重十分类似。
戏剧复调还牵扯出与复调音乐类似的“协调统一”的问题。前文提到的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主要强调了复调各声部间的相互独立性、矛盾性和对抗性。事实上,来自音乐领域的复调虽然讲究各声部的独立性,但又具有协调统一的内在需要。在复调音乐中,“二音对一音”或“四音对一音”等对位类型,意味着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此消彼长和矛盾统一,协和音会受到不协和音的挑战,不协和音在动态中会走向协和音。总体上看,哪怕一种新的、反常的、看似混乱的音乐风格,“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它逐渐为理性所控制,不断规范化,经过一个以具象化为标志的格式塔化过程”。[14](P352)“非音乐类”戏剧中的语言若符合审美规律,同样暗合了类似于谱曲或演奏乐曲的协调统一中枢活动,只不过相对隐蔽一些。“在语言生理学中,整合与协调的观念再次作为与原子主义的妥协而不是作为对它提出的问题的解决而出现”,“属于这些协调中枢本身的(正如属于钢琴师的)乃是对强度和音程的分配,是对音符的选择和对连续顺序的规定,一句话,是对知觉或运动的结构属性的转化”。[15](P134)与语言生理学和复调音乐类似,戏剧复调也将矛盾性和张力纳入整合和协调的概念中,以确保戏剧的有机完整性和自足功能。“这一协调的真正名字就是‘自动性’。当一列火车所有的门都关上后,正是这一机制保证了出发信号的发出。”[15](P135)
在《名字》中,戏剧复调在提供复杂幽微的矛盾性和张力的同时,也在为全剧的统一性做准备。比如贝厄媞(剧中的“女孩”)的男友(剧中的“男孩”,也是贝厄媞腹中胎儿的父亲)和贝厄媞的妹妹上楼后,贝厄媞和前男友比杨恩待在沙发上,“她(贝厄媞)躺下来,头放在他(比杨恩)大腿上”,过了一会儿妹妹走了进来:
妹 妹:他(指“男孩”)说他想睡了/想看会儿书(妹妹走过去在扶手椅上坐下。沉默。)/我们打牌好吗
女 孩:不别烦我
妹 妹:我只是问问
比杨恩:他喜欢看书
女 孩:他老是在看书
妹 妹:(笑了起来。)他坐着看了一整天书了
比杨恩:哈看书[8](PP103-104)
在比杨恩到来后,贝厄媞疏远了“男孩”,与比杨恩有了亲昵动作;“妹妹”反而暂时更关心“男孩”。“妹妹”的打牌建议烦扰了贝厄媞,这是她们姐妹之间戏剧复调的矛盾性,但“妹妹”也引领了“他看书”的话题,由此引出比杨恩、贝厄媞、“妹妹”三人对“他看书”的“复调”的相互协调。他们不仅在对话中有各自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未论定性”,而且矛盾地统一在流动的时空里。这些不同角色的单独话语的意义极不明确,但是当它们按照类似于音乐的结构被组织出来、相互映照时,就变得意味深长。这是因为,戏剧中不同角色的语言如同音乐的音符,“单独来看,这些音符具有一种不明确的含义,能够进入到无限多的可能组合之中,而在曲调中,每个音符都受制于前后音符,都为表达某种并不包含在任何一个音符中,但把这些音符内在连接起来的东西而起到自己的作用”,“协调因此是对意义整体的创造,是对某些关系的创造”。[15](P136)如同音乐,这种相互关联性和整体协调性,都属于戏剧艺术(包括戏剧复调)的内在需要。
三、音乐性对全剧的定调与“数理—艺术”作用:
抽象与具体,极境与丰富性
上文主要是从音乐的节奏(包括变奏)、复调这两个方面,相应地联系戏剧语式和戏剧时空来探讨福瑟剧作中的音乐性,而从这里开始将从更深、更具综合性的层面,即从数理抽象化与艺术情感具体化的高度结合来探讨福瑟戏剧与音乐的共通性。
福瑟剧作重视始发点的场景,并常常将始发点场景前后呼应或贯穿始终,类似于作曲家重视起始音对整部作品的定调作用。“只要刺激的前面一些元素被给出,它就把这一规律显现出来,就如某一曲调的那些起始音符确定了这个曲调整体的解决方式一样。”[15](P136)在为始发场景定调后,福瑟又进行了全面的极境化的推动。这种推动的轨迹从大方向上说也是形态各异的。“他作品中明显的音乐特征是上升或下降的韵律、简洁或宽阔的拱形旋律”,“复调或和谐的短句、成调与不成调的旋律配合;我们甚至可能谈到赋格曲和奏鸣曲、室内乐、独奏等等”。[3](P239)以上对美术家兼音乐演奏家克利绘画中音乐性“推动轨迹”的比拟,套用在福瑟的剧作上也大致不错。
这些剧作音乐化定调的始发点往往是某一被简化了的场景:有的以简代繁,如海边被简化的屋子、家里的客厅等;有的干脆充分利用舞台假定性,以无代有,如《我是风》的场景发生在一艘想象中的船上。接着便是集全剧之力向某种“极境”推移:有时,全剧就结束在这种“极境”之中,如《死亡奏鸣曲》《我是风》;有时,“极境”渐渐消退,但貌似“无事”的“悲喜剧”却已经发生,如《有人将至》《名字》。当然,这些“极境”有的极严峻,也有的极脆弱、极犹疑、极细微,关键在于“极”。它们或是指某种脆弱的平衡被无情地打破,如《有人将至》中“你和我单独在一起”的平衡被第三者打破;或是指极为细弱的情感之弦绷紧到极限,如《名字》中贝厄媞、其现任男友、其前男友三者间的关系,甚至还要扯上父母、妹妹等所有人的关系;或是指人物关系走向死局,如《秋之梦》中上一段婚变不可避免地与这一段婚恋相互缠绕,留下致命的创伤,使家庭关系、人伦关系走向坟墓;或是企图在空间的尽头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时间的尽头—寂灭,如《死亡奏鸣曲》中“女儿”循着“朋友”在海天之间的幻影投海而死;或是指向比死亡还要抽象的东西,如《我是风》中令“一个人”既害怕又痴迷并抑制不住地要成为的东西—飞向外海的“风”。正是这种音乐化定调和向极境的全面推动,使福瑟剧作在舞台上有了矛盾、冲突、高潮、低潮、悬念和张力。
这种向极境的音乐性推动与演进,如果站在抽象、简化的角度上,可进一步从音乐与数学、物理学的关联性来分析。音乐,尤其是音乐的演奏过程是具体、丰盈的,但乐谱即使再细腻完整,也仍属于抽象化的符号,而乐理、音乐现象又往往可被简化为数学公式。“音乐理论中比较艰深的部分,如律学、和弦等,对应的数学知识并不复杂,主要是比例(分数)、对数等,而像振动方程的解、傅里叶级数等数学内容,对应的音乐现象反倒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如泛音列、音色、音高与弦长之间的关系等。”[16](PⅣ)而从基础角度说,声音的高低、强弱、持续长度、振动频谱的物理属性分别对应了音乐中音高、力度、时值、音色的概念。[17](P1)正因为乐理与数学、物理学规律深度契合,所以充满音乐性的福瑟剧作,也具有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抽象的一面。福瑟创作中的极境配上了戏剧人物的关系图与行动线(与音乐可被抽象成曲谱、可被换算成数学公式一样),可被视为一种简化、抽象为“向量图”的“力之疆域”或“心理疆域”,这也许可以从注重数学与物理学的拓扑心理学那里得到解释。“心理学的体系便欲采取伽利略式的思想”,“行为等于人乘环境的函数”,“一方面为目的物,一方面为个体,目的物引拒个体,于是乃有所谓‘向量’乃有所谓力之疆域(field of forces)。而假若目的物和个体之间置有一道障碍,则疆域上的势力则增加复杂性”。[18](P19)有了性质不同的“障碍”的引入,心理疆域的动力性质也变得复杂起来。“一个疆界对于跨越的抵抗力甚为重要。这个抵抗力可自零而至于无穷大,有各种可能的不同程度。不明确的和明确的疆界都莫不然。”[19](P128)
在音乐的数理抽象性视域下,心理疆域中的“抵抗力”与“障碍”是如影相随的,在戏剧中就呈现出相应的戏剧矛盾、人物性格冲突,因此,福瑟剧作中极境下的每一组人物关系、每一个人物的心理都可以被抽象出“障碍”与“抵抗力”之间博弈的图示。前文说过,福瑟剧作中“极境”的“极”并不一定指“极庞大”,也有可能指“极微小”,这带来“疆界”中“抵抗力”与“障碍”之间博弈的极度困难性或极度纠缠性。比如,《有人将至》中“她”对陌生“男人”留下的写有其电话号码的纸片的“抵抗力”与陌生“男人”对“她”的吸引力(即“障碍”)之间有博弈的过程,从简化的、抽象的、极境的角度说,最后这个“抵抗力”被“吸引力”牵绊住了。《秋之梦》中的“男人”作为不忠的前夫、不负责任的父亲、不孝的子孙、不坚定的恋人,他的心理疆域受到多股外部力量的冲击。他总是暗暗地与前妻(包括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未出场的儿子)、父母(包括祖母的墓碑)、“女人”这三种施加于他的无形的力量相抵触。其他人并未对他怒骂不已,但前妻的诸如“高特(儿子)死了/可你不在乎/我早就知道/你一点儿也不在乎”等言语,母亲的“你要杀死我了/你就是我的死亡”等言语,以及前妻与“女人”相互要求对方“放他走”等言语,却可以抽象出不同性质的“障碍”或破坏力,从各个方向撕扯他的心,把他推向死亡。[7](PP258-260)他无力抵触的那一刻,就是他死亡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抵抗力”为零的那一刻。总体上看,福瑟剧作中的“极境”正是“不容易通过的疆界”,“困难到了极端时便为不能跨越的疆界”,正如“不能游水的人无法游过对岸”,而这种“极境”往往是通过缓慢、迂回的过程展示其困难程度的。[19](P124)
如上文所述,音乐之抽象的一面可与数学、物理学相类比,然而,音乐另一方面又有艺术之情感内容的具体性和丰富性,“无论一首表情的音乐作品的曲式是怎样的错综复杂,它仍然只不过是作曲家把有意义的次序用在表情的术语上,从而表现对待生活的情感态度的方法”。音乐之具体的一面在坚持“音乐是情感语言”的学者那里被着重强调。如同音乐把情感丰富性注入抽象的数理式曲式中,福瑟戏剧的极境之中被注入丰富的人物性格,简化的舞台背景中被注入丰富的思想内容。根据上文,有多少个数值的“抵抗力”与“障碍”之关系的向量图,就有多少种戏剧人物关系,因而这些看似简化的极境被赋予了多义性,极严酷、极细弱、极犹疑的情境赋予“障碍”的复杂性,造成了心理疆界的动力变动的复杂性。
“我们的事例可表示障碍对于移动有不同种类的抵抗。它可有不同程度的‘坚实性’,不同程度的‘僵硬性’(rigidity)或‘弹性’”,“这里的阻力可称‘摩擦’。最后,障碍还可能有多少带有渗透膜(permeable membrane)”。[19](P125)与音乐之艺术丰富性的一面相类似,福瑟剧作中复杂的“摩擦”,也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弹性”。有些涉及生死的“摩擦”往往不是“硬摩擦”,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为“障碍”贴上“渗透膜”,也使面对“障碍”的“抵抗力”迂回起来,如《死亡奏鸣曲》中“朋友”对“女儿”迂回的、逐步加强的致命诱惑及“女儿”对“朋友”复杂的迷恋过程,《我是风》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互纠缠直至消亡的摩擦与对抗关系。有些表面上看只是生活的涟漪,深层次看却是心中的地震或雪崩,人物心理疆域的“障碍”不可谓不极致,心中的“抵抗力”不可谓不强烈,如《名字》中贝厄媞现任男友“人在屋檐下”的郁忿与无奈,《秋之梦》中“男人”在各种迂回的指责和压力下的突然死亡等。总之,福瑟戏剧为简化、抽象的极境中的“心理疆域”带来复杂的、往复变幻的“弹性”或丰富性,为极境注入“结构变化的动力条件:流动性、弹性、可塑性”。[19](P160)
这种简化的极境与丰富的情感内容之完美结合,依靠的是戏剧演出呈现的自足功能,就如同音乐演奏呈现的自足功能一样。就“抽象”与“具体”的相互依赖程度而言,福瑟剧作能与音乐相比拟,却不能与极简主义绘画相比拟。福瑟剧作所追求的简化的极境在某些方面虽然类似于上世纪美术界所称的“现代极简主义绘画”,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有异于后者,因为福瑟剧作的目的是为了上演“极境式戏剧”,归根结底是“戏剧”。当然,现代极简主义绘画理论自有其锐利性,“格林伯格认为‘现代艺术’对于现代精神的体现即在于: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以抵达自身的限制性所在,不断地通过清除自身身上的附加成分而寻找到‘不可还原之物’”,“最终客体的‘体积’被碾压成‘轮廓’”,“体积感与底面之间形成‘挤压与承受’‘抵抗与反抵抗’的辩证关系”。[20]某种层面上看,福瑟剧作在简化的极境中确乎在靠舞台上少而精的、“不可还原之物”的“挤压与承受”“抵抗与反抵抗”而产生张力,然而,格林伯格的上述“极简主义”理论是以绘画为主要审美对象,而福瑟剧作即使有一些极简主义的倾向,也依然是戏剧,它们有“轮廓”,更有“体积”和“过程”,这就注定它们不可能真的被“碾压成‘轮廓’”。
与格林伯格所定义的“极简主义绘画”不尽相同,福瑟剧作中的“不可还原之物”被简化成类似于音符的语言和节奏单元仅仅是开始,之后它们必须要有一个类似于音乐的有机组合的时间过程,必须要有不折不扣的演出呈现过程。可以说,是音乐性在为福瑟剧作极简的场景或极境输血,而音乐本身就是数理抽象化与艺术情感具体化的高度结合,这就形成了福瑟剧作抽象与具体的双重性:既是简洁的,又是丰富的;既有骨骼,又有血肉。“音乐修养让他有了一个节拍器—故事不是踩在地上的脚,而是步伐与步伐之间的空隙”,“如果你快进,就必然会遗漏东西”。节奏并不仅仅是节奏,“步伐与步伐之间的空隙”并不是空白,静默、停顿之处并不是虚空,福瑟剧作在追求简化的“极境”的同时尽力铺叙人物情感、人物关系、人物矛盾的复杂性与细腻性,最终形成一个活的、有血有肉的作品。由于紧紧抓住音乐性的流动演进过程,所以福瑟剧作的“极境”是人物性格、舞台事件深度参与和组织下的“极境”,而不是“纯绘画”意义上的“碾压成轮廓的极境”。这不仅体现在福瑟的剧作中,更体现在福瑟剧作的演出中,例如2014年上海当代戏剧节的“福瑟之繁花”单元的五部亚欧剧目演出,都可谓用尽手段,在极简和丰富性之间游走,在静默、停顿之处填充丰富的气息、氛围、情绪和心理活动。
余论
阐释福瑟剧作中的音乐性,目的在于揭示福瑟的音乐素养与其剧作风格的紧密关系,在于揭示节奏化、复调的对立统一性、数理抽象化与艺术情感具体化的高度结合等音乐要素和音乐性美学规律对这种风格化戏剧创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挖掘其中音乐性的生发途径,可为这种被指“难演”却又有强烈演出意识的当代剧作提供另一种表导演阐释思路。话说回来,戏剧(尤其是“话剧”)与音乐相比,仍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必须首先遵循自身门类的艺术规律。因此,我们在探讨中注重的是不同艺术门类的美学相通之处,而并不需要(也无法)将福瑟剧作中的台词或动作与真正的音乐旋律、曲式结构逐一“对号入座”。也许,我们更应该像克利绘画的鉴赏者“用内在的耳朵”来聆听其绘画中的音乐那样[3](P123),要用内在的耳朵聆听福瑟这些“非歌剧”“非音乐剧”的剧作中的音乐。
参考文献
[1]STOKKE Øyvind.序言[M]//约恩·福瑟.秋之梦:约恩·福瑟戏剧选.邹鲁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邹鲁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M]//约恩·福瑟.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邹鲁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维尔·格罗曼.克利[M].赵力,冷林,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4]于贝斯菲尔德.戏剧符号学[M].宫宝荣,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5]WORTON Michael. Waiting for Godot and Endgame: Theatre as Text[M]// PILLING Joh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ckett.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M]//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外国戏剧百年精华(上). 施咸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约恩·福瑟.秋之梦:约恩·福瑟戏剧选[M].邹鲁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8]约恩·福瑟.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M].邹鲁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9]凯瑟琳·乔治.戏剧节奏[M].张全全,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10]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册)(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1]ESSLIN Martin.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Third Edition)[M]. London : Methuen Publishing Limited,2001.
[12]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M].于秀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5]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6]王杰.前言[M]//音乐与数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7]王杰,编著.音乐与数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8]高觉敷.1942年版译序[M]//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9]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0]舒志锋.知觉与物性:梅洛-庞蒂与极简主义艺术[J].美术研究,2019(4).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投稿须知
《戏剧》是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艺术类学术期刊。本刊试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者来稿须标明以下几点:
1.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位。
2.基金项目(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3.中文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篇幅为150-200字。
4.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大致对应,长度为80个英文单词左右。
5.中文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6.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大体对应。
7.注释:用于对文章正文作补充论说的文字,采用页下注的形式,注号用“①、②、③……”
8.参考文献:用于说明引文的出处,采用文末注的形式。
(1)注号:用“[1]、[2]、[3]……”凡出处相同的参考文献,第一 次出现时依 顺序用注号,以后再出现时,一直用这个号,并在注号后用圆 括号()标出页码。对于只引用一次的参考文献,页码同样标在注号之后。文末依次排列参考文 献时不再标示页码。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
a.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M].
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外文版专著、期刊、论文集、报纸等: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姓在前,名在后,之间用逗号隔开,字母全部大写。书名、刊名用黑体。尽量避免中文与外文混用。
来稿通常不超过10000字。请在来稿上标明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电话,发送至学报社电子信箱:xuebao@zhongxi.cn。打印稿须附电子文本光盘。请勿一稿多投,来稿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录用或修改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发现有一稿多投或剽窃现象,对我刊造成损失,我刊将在3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投稿。来稿一般不退,也不奉告评审意见,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
《戏剧》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也未单独开设任何形式的网页、网站。同时,中央戏剧学院官微上将选登已刊发文章。
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欢迎各位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中央戏剧学院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 “zhongxi_1938”,或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关注。
网站:http://www.chntheatre.edu.cn/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