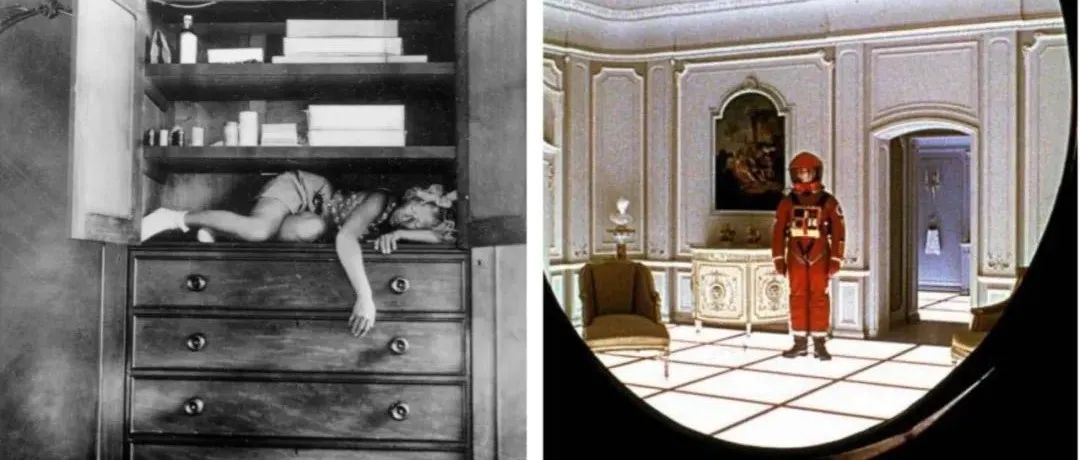- 0
- 0
- 0
分享
- 特邀观察员 龙星如 | 类型穿越带:人工智能、量子或前沿之魅
-
原创 2022-0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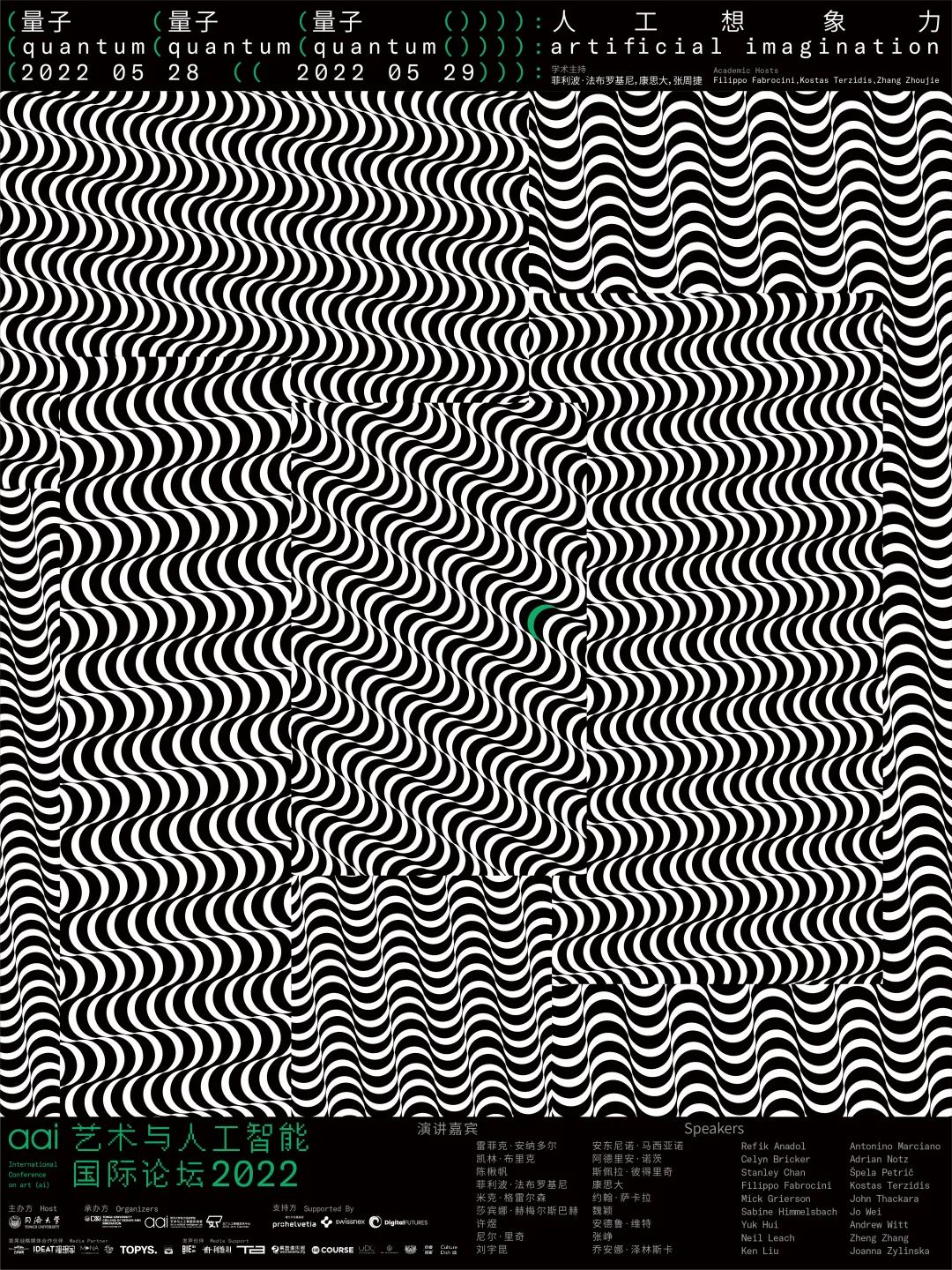
( 论坛回顾 ( )):
由同济大学主办,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艾厂人工智能中心(Aiiiii Art Center)共同承办的第二届aai艺术与人工智能国际论坛于2022年5月28、29日成功举办。来自计算机科学、技术哲学、物理学、艺术及文学创意领域的18位演讲嘉宾,围绕会议主题“(量子(量子(量子()))):人工想象力”,结合其专业背景进行了共计四场的演讲及对谈。截至5月29日,本期会议共触达全球高校800余所,在7个媒体平台收获11万以上的观看量,25+媒体进行报道,总曝光量超过22万,相较于往年增长近五倍。
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本次论坛的三位学术主持康思大(Kostas Terzidis)、菲利波·法布罗基尼(Filippo Fabrocini)和张周捷在论坛首日开幕式上就人工智能艺术发表欢迎致辞。娄校长强调了技术助推艺术、设计创新的重要意义,对会议主题中量子的思维方式表达了期待。三位学术主持简要阐释了人工想象力、人工智能艺术、量子逻辑对当下环境的影响和启发,并追问人工智能作为触达未来的新的可能性。
从量子概念全方位的展开,演讲嘉宾们从文化、创意、所有权等方向,分享了他们对人工想象力的反思。在对谈环节,各领域思维的碰撞也为观众、特邀观察员们提供了新的灵感。
本次论坛邀请了数位策展人、艺术家及学者作为特邀观察员,以新生代艺术、文化实践者的视角对论坛议题及部分嘉宾的演讲内容进行解读和延伸。特邀观察员的人类想象力佐以人工想象力之议题,为人工智能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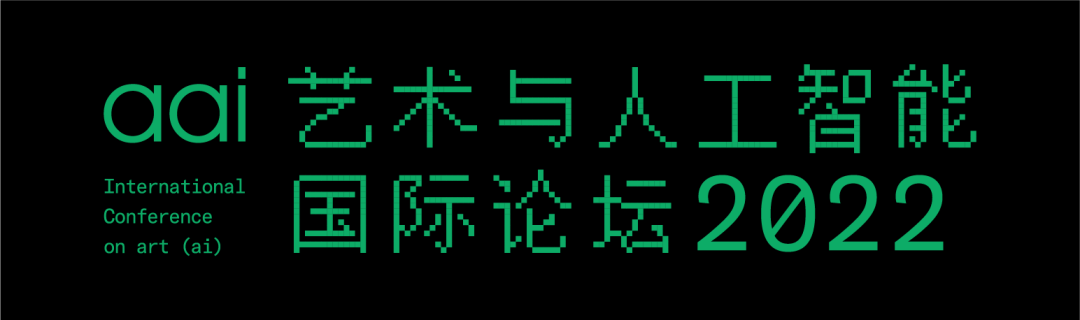
( 特邀观察员 ( )):
龙星如 Iris Long
( )
策展人,研究者

策展人,写作者,研究方向为艺术创作与数据、环境及技术的关系,以及科技的心理地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博士就读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前沿实践方向。译《重思策展:新媒体后的艺术》并获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出版物提名(2016);第一届IAAC国际艺术评论奖英文入围评论者;策划展览包括《撒谎的索菲亚和嘲讽的艾莉克莎》(Hyundai Blue Prize策展人奖, sophialexa.com),《他山之石,新代理人》(PSA青策计划大奖),第三届今日未来馆《机器人间》等,她也为艺术家刘昕、Lauren Lee McCarthy等策划国内首个个展。2019年担任ISEA电子艺术研讨会国际评委。2020年担任计算机图形学会议SIGGRAPH ASIA艺术板块国际评委。研究发表于ZKM媒体艺术中心“艺术与人工智能”会议,香港城市大学运算媒体艺术国际论坛(ISCMA),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数字人文与艺术研究国际论坛,ISEA电子艺术研讨会等。她也参与过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商汤科技、蓝箭航天等科技企业的项目。2021年,她发起了“端口:云下贵州”项目,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基础设施的长期调研和策展项目。个人网站:irislong.xyz
( 类型穿越带:人工智能、量子或前沿之魅 ( )):
撰文:龙星如
“前沿”科技一如既往地让人同时感到谨慎和迷恋。谨慎在于它似乎提示一种线性技术时间,甚至是由技术所决定的时间。这些看似站在“前线”的技术创新者,很可能在我们的认知跟上之前,就决定了我们实际将经历的未来。迷恋在于“前沿”依然象征着未曾有过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和突破重复模式的新鲜感。尽管在吉欧夫·阔克斯(Geoff Cox)等研究者看来,被“后数字”所概括的我们这一代,因为媒介文化的极度不同步性(asynchronous),“新”或“旧”之类的时间戳开始变得不再有效[1]。
艾厂人工智能艺术中心近期举办了一次跨学科论坛,aai艺术与人工智能国际论坛,依然从艾厂主要研究的人工智能课题出发,并将“量子”作为看待人工智能艺术的视角提出。这两个领域(当下的人工智能研究,和作为基础学科的量子物理[2])之间并没有显在/必然的关联——除了在公共认知中相对“前沿”这一属性之外。故而,这场论坛也将围绕“前沿”思维可能生长出来的想象力与争议,较为诚恳地铺陈开来。围绕科技的艺术实践是否“喜新厌旧”?如果说对于理论研究者和艺术家来说,仍然很难跟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形式的突然连续和冗余[3],那我们是否归根结底仍在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中?当我们论及“前沿”时,它究竟在某些固定的学科建制中产生,还是会发生在学科之间的跳跃行动中——此处并非将“前沿”等同于增长意义上的“良性的”、“值得称颂的”,而是更多地考虑它以“未被实践过”的形态出现时,给具体的个人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毕竟,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回应的是,作为个体,为何人工智能或量子研究与我们有关,它是否被允许无关,这些前沿概念何以不成为装裱在墙上的勋章、填充空虚的安慰药、或是《时髦的空话》(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里让科学家感到反感的词意混淆和滥用,而成为具体的方法、脑洞乃至催化剂。

Machine Hallucination, Courtesy of Refik Anadol Studio
格兰特·泰勒(Grant Tayler)在一本综述性的文集《当机器开始创作艺术》中,提及当“计算机艺术”在1965年进入艺术视野时,计算机本身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一个积累了复杂文化意义的人工制品[4]。这对于人工智能艺术来说,也是适用的——“人工智能”携带着极为复杂的文化意义进入了艺术语境,尽管它的物理载体及模型细节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抽象。如果不简单将“人工智能艺术”视为新技术工具和艺术实践的嫁接,那么理解“人工智能”内嵌的文化语境是如何流淌进现实生活,似乎是有必要的。机器学习目前存在的关于算法偏见、数据集漏洞、“好用”的相关性和黑箱遍布的状况,以及产业链条背后的劳动现状、资源采掘及穷尽的倾向性,一定程度上已经使得“技术中性”的想象开始破缺和渗漏,“前沿”可能是非客观的、未完成的、不完备的。事实上,当且仅当一种技术形态如此参差地出现时,它才具备更高的作为创作回应对象的潜能——如果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与艺术的接驳仅仅是艺术家对预训练模型的创造性使用,并仅仅带来形式上“未见过”的创新,那或许低估了创作者对其文化意义的敏感。

艾达与她的作品 摄影:Nicky Johnston
在牛津大学网络学会及工程科学科系发布的题为“人工智能及艺术”(AI and the Arts: How Machine Learning Is Changing Artistic Work)的报告中,作者强调了“人工智能艺术”并不必然意味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心”——“进尽管技术能力是一种被高度重视的技能。”报告进而指出,“使用机器学习模型所需要的新活动既涉及到与以往创作过程的连续性,也涉及到与过去实践的断裂。主要的变化涉及围绕生成过程的创造性工作流程的重组。”[5]换言之,对“前沿”的祛魅一方面可能将其偏离中心,另一方面,也涉及将其视为交织着文化语义的对象而非纯粹技术对象的理解角度。这一点在艾厂举办的aai艺术与人工智能国际论坛2022中,乔安娜·泽林斯卡(Joanna Zylinska),尼尔·里奇(Neil Leach)和莎宾娜·赫梅尔斯巴赫(Sabine Himmelsbach)的分享里,均可以管窥。尼尔·里奇通过对“人形机器人”的祛魅,点明了附着在技术之上的想像性解释空间(文化意义的某一层面)的存在。乔安娜·泽林斯卡在研究中进一步拆解了人作为“创造力”的拥有者、仲裁者的角色,并强调人的创造力本身蕴含“非人”的要素,这也进而回应了罗西·布来多蒂(Rosi Braidotti)提出的某种激进的批判后人类论点——布来多蒂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后人类主义本身作为整体,已经被技术(不管是基因编辑还是信息技术)所高度媒介化,故而当我们谈到人与“非人”的纠缠时,这种纠缠极为底层(亦即,几乎蔓延在所有的认知、制造和运用细节中)。[6]莎宾娜·赫梅尔斯巴赫也进而通过对展览“纠缠现实”的讲解,延展了对于这一“纠缠”的论述。

AI and the Arts: How Machine Learning Is Changing Artistic Work
另一种关于“前沿”的迷思可能存在于技术/知识/学科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如果说机器学习已经相对普及的话,量子理论尽管已经有百年历史,仍然停留在极难被真正科普的阶段,也因此成为极为容易被普遍滥用或过度简化的领域(一个常见的谬误是把宏观态和微观态混为一谈)。“前沿”是否会因为对专业知识积累要求高、难被普及、路径闭合等特征,而进入一种不平等局面——在部分人眼中,技术“前沿”对艺术的压倒态势,为一种不平等(科技艺术的历史并非没有见证过对工程与技术过度崇拜,而将创作者边缘化的局面),而这种结构之下,“前沿”其实也容易被刻板印象化,因其技术浓度而成为无法被穿刺、挑衅或撼动的对象,而被锁死在学科内部,丧失了真正渗透的可能,这对于“前沿”来说,似乎也是不公平的。或许有必要追问,对一个领域理解上的“平等”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必须都成为专家?如果答案为“否”,我们究竟如何可以“跨越学科”?

《何以在世界尽头创造艺术》,娜塔丽·勒夫雷斯
娜塔丽·勒夫雷斯(Natalie Loveless)在《何以在世界尽头创造艺术》中,提出一种有趣的视角,她认为跨学科工作的核心仍然是问题导向而非身份导向的。(用她的原话说,跨学科从来不是关于“看!艺术家也能做研究”或者“科研人员也能创作艺术”[7]这样的身份斗争)将不同学科的声音和实践带到同一张桌子上,事实上可能扰动那些既定研究-创作学科实践中知识/权力的传递,进而使得一种“响应式实践”(responsive practice)成为可能。这些“问题”的来源,很可能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既定学科——这一点在艾厂此次论坛的分享者中,也可见端倪。比如对刘宇昆来说,他关注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途径”这一话题,实际上并不严格受到科幻写作模式和作为写作合作者的NLP模型的边界束缚,当新的智能模型出现时,同样的话题仍然可被继续探讨。安东尼诺·马西亚诺(Antonino Marciano)的演讲也具备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量子物理究竟如何关联到人工智能领域。上述响应式实践的产生,在于由“以学科为导向的理解方式”之外的空间中所产生的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勒夫雷斯所转引的、由乔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和苏珊·雷·斯塔(Susan Leigh Star)(1999)提出的“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的概念[8],在这里或许也值得参考。“边界对象”即本身位于几种实践地带之间的,具有强可塑性的对象,这些对象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可以保持跨领域的身份,在共用时可能呈现弱结构的形态,在领域内使用时又具备强结构的可能。在边界对象和响应式实践的思路下,我们或许可以暂时将“前沿”与“非前沿”、此学科与彼学科从金字塔关系或其他强结构关系中松绑,并放下以学科作为第一身份认同的纠结,去看待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研究或者其他“前沿技术”在内的工作,和艺术领域之间发生的交叠和对话。如果我们终将可以把“学科”从身份变成行为,“变成一个人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是的事情”[9],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行为铺成一种类型穿越带,而在这样的穿越带中,有价值的工作终将出现。
注释:
[1] Cox, “The Post-digital and the Problem of Temporality,” 151; see also Florian Cramer, “What is ‘Post-Digital,’” Postdigital Aesthetics: Art Computation, and Design, eds. David M. Berry and Michael Diet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5), 12–26.
[2] 注:此处仅指作为基础研究的量子物理,不包括其应用比如量子计算。
[3] Taylor, “When the Machine Made Art: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Computer Art,” 11.
[4] Taylor, “When the Machine Made Art: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Computer Art,” 14.
[5] 见:https://www.oii.ox.ac.uk/news-events/reports/ai-the-arts/
[6]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144.
[7] Loveless, “How to Make Art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A Manifesto for Research-Creation
,” 28.
[8] Loveless, “How to Make Art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A Manifesto for Research-Creation
,” 32.
[9]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艾厂人工智能艺术中心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