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 0
- 0
分享
- 王世巍:剧场表演与观看行为的博弈——雅克·朗西埃观众理论的审美视域
-
2022-04-18
剧场表演与观看行为的博弈
——雅克·朗西埃观众理论的审美视域
王世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雅克•朗西埃认为,有关剧场观众观看行为的争论,其实是一个比舞台表演者悖论更具有本原意义的问题。作为西方当代激进平等哲学的代表,朗西埃的理论立足点是个体感知的“歧感化”凸显。舞台下的形式化观众整体,其实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感知经验和感知倾向的主体。平等的舞台表演,不是通过景观式的呈现对被视为统一体的观众进行整体包围,以期让台下等量且均质地追随并执行台上的感觉分配计划。它应该是要激发、鼓励并且接受观众的“歧感”显现,从而为个体的感知自由和审美解放提供契机。
According to Jacques Rancière, the debate on the spectatorship of the theater audience is in fact a more fundamental issue than the paradox of performers. Representing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radical equality, Rancière's theory has its basis highlighting the "dissensus" of individual perception. Rather than a formalized whole, the theater audience should be regarded as individual subjects with independent perceptual experiences and perceptual tendencies. An egalitarian theater performance is not a landscape presentation that surrounds the collective audience, with the intention of having them follow and execute the sensory distribution plan in equal quantity and homogeneous quality. Instead, it should stimulate, encourage and accept the "dissent" manifestations of the audience, thus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individual perceptual freedom and aesthetic liberation.
关键词丨Keywords
雅克·朗西埃 剧场 平等 歧感 审美
Jacques Rancière, theater, equality, dissensus, aesthetics
一、朗西埃的质疑:
剧场果真是一个感知共同体吗?
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以下简称朗西埃)是当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他的理论研究以政治哲学为中心,进而延伸到了文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在这其中,朗西埃有关当代电影与戏剧表演、文学政治以及艺术审美体制等系列问题的相关观点和系列论著,近年来也已经在欧美哲学、美学以及艺术理论界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影响力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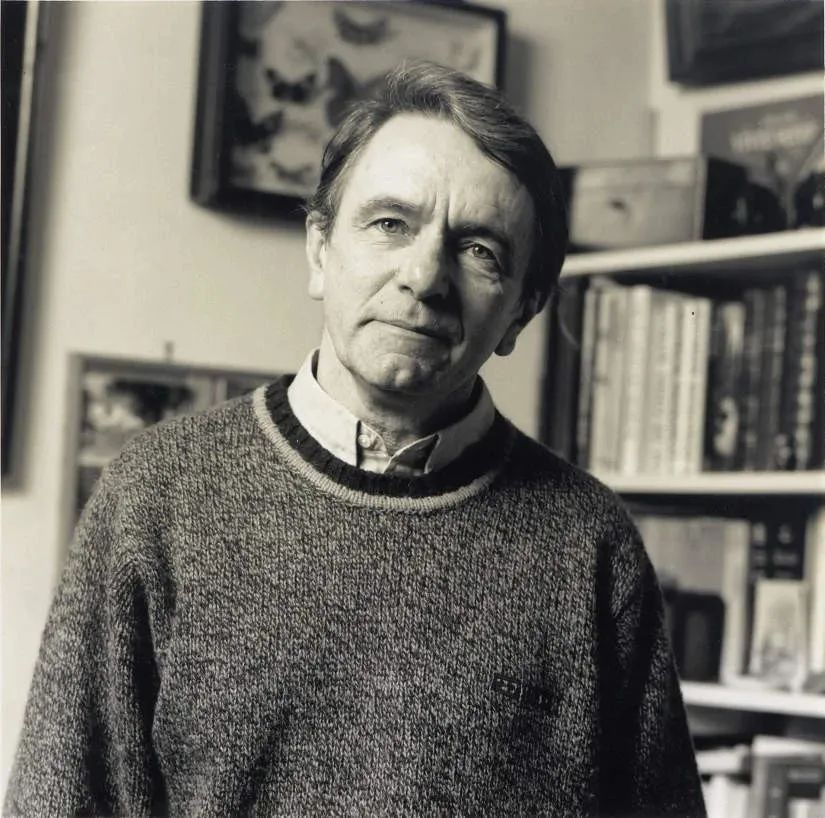
雅克·朗西埃
2004年8月,在法兰克福第五届国际夏季艺术论坛的开幕式上,朗西埃受邀发表了题为《被解放的观众》(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的主题演讲。2013年5月,朗西埃应国内学者的邀请,在中国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学术交流。这其中的5月15日,朗西埃在四川美术学院,再次发表了以戏剧表演和观众感知为核心议题的演讲—《说、演和做:在艺术和政治之间》。
根据朗西埃自己的陈述,《被解放的观众》的演讲内容是他对自己在艺术表演学院被问及的、如何看待剧场里的“观众行为”(spectator ship)之问的回应和思考;而他之所以会被问及如何看待观看行为问题,则与他在其教育著作—《无知的大师:关于知识解放的五堂课》(The Ignorant School 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中所阐述的、在无知教师与学生求知之间的、关于智性平等与智力解放的系列观点相关。

《The Emanicipated Spectator》(被解放的观众)
在《被解放的观众》这篇演讲中,朗西埃认为贯穿整个西方戏剧表演理论论辩史与改革史的矛盾核心,其实可以被简要地归结为一个悖论,被朗西埃称之为“观者的悖论”(the paradox of the spectator)。朗西埃甚至评价认为:“观看者悖论也许是一个最终要比著名的表演者悖论更关键、更具有本质性意义的悖论”[1](P6)(a paradox that may prove more crucial than the well-known paradox of the actor)。因为自从20世纪以来的戏剧理论家开始把观众列为戏剧以及舞台演出的直接对象和目标要素之一,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戏剧的表演方式与演出的实际意义等问题时,观众在剧场里的角色和实际作用就已经远非看上去那般的默默无闻。换言之,自从观众上升成为戏剧演出和舞台效果的构成性的目标化要素,西方的戏剧研究者们几乎无一不是在对观众的静坐式观看行为大发疑虑,并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于是,朗西埃便总结认为,近代的戏剧理论家们(如著名的布莱希特与阿尔托)都认为“观看行为是个坏东西”。因为在现代、后现代戏剧主义者的眼里,观众在台下的静观不仅与理性的认知、思辨相对立,而且也与舞台表演所指向和试图勾连的实际生活和行动能力背道而驰。
因此,为了挽回戏剧艺术最初所追求的东西—知识和行动(引导行动的知识和追求认知的行动),戏剧必须寻求改变,而戏剧理论家寻求改变的宗旨和鹄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观众”的剧场。“在那个剧场里,观众将不再只是个看客。他们学习事物而不只是被图像所虏获,他们将变成一场集体表演中活跃的、直接的参与者,而不再是被动的、与舞台无关的旁观者。”[1](P8)在朗西埃看来,为了使观众实现这个转变,西方的戏剧理论家们提供了两种在原则上相互抵牾的代表性方式:布莱希特的史诗、理性戏剧和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一方面,观众必须离得更远;但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得抹去一切距离”[1](P8)。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方式—朗西埃将其概括为“远距离的探究和生命活力的彰显”(distant inquiry and vital embodiment)—一方面引导着对建立新式剧场的尝试;另一方面则却也从根本上对剧场本身的存在意义提出了质疑。
在朗西埃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有关戏剧改革的主张与计划,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然而,朗西埃指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并不是究竟应该如何去改革,而是反思这个改革行动本身的必要性以及其合理性究竟在哪里。他认为有关戏剧变革的相关理论运动,其中归根结底的实质问题其实是,无论哪一种改革方式,它们都预设了一个隐蔽的前提。这就是它们都把剧场空间里的观众群体,视作为一个类似于自然有机体的生命整体,并且默认这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感知方式和感知能力。“自从德国浪漫主义拉开帷幕,剧场概念就一直与生存共同体的观念(the idea of living community)密切相关”[1](P10),朗西埃意识到在这个预设性认知里所潜藏的错误与风险。这是因为,偶然汇集到一个剧场里的万千观众,果真是一个紧密的、统一的感知共同体吗?这正是朗西埃关注和所要反驳的焦点问题。
朗西埃承认,从外部的直观视角来看,尤其是对那些置身于舞台之上的表演者和策划者而言,他们的确很容易把台下观众看作是一个整体化了的、紧凑齐一的群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由观众构成的形式整体在其内部、在其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内在无差别的、均质性的感知共同体。朗西埃这个论点无疑是独到而深刻的。因为一旦戏剧的导演们和编剧们习惯性地把台下的观众预设为一个统一的感知整体,那么这个被视作齐一的整体,将会悄然地影响到包括演员、导演,甚至是直接影响到整个表演的设计、进程以及走向。
由于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演员们和幕后的编剧与导演们,正是为这些集体出席在同一地点的人群而表演,所以这个预设性的认知将不仅伴随着表演前、表演过程以及表演结束,而且由于他们的任务与目的就是要给剧场里的观众整体提供表演、制造图景,所以这就容易让他们形成一种单向性的认知和判断,即他们要努力给这个共同体提供某种目标性的唯一感(unique sense)。当“剧作家越是不知道作为集体的观众应该做些什么,他就越是觉得有必要把台下的观众看成一个集体,将他们单纯而又偶然的聚集转变为一个共同体”[1](P12)。
朗西埃之所以认为这样的群体(诸如剧场里偶然聚合到一起的观众)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或者说有实质意义的共同体概念,这其实是基于他对“政治”与“平等”概念的批判性解释。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歧义:政治与哲学》(Disagreement:Politics and Philosophy)中,朗西埃曾经用人类的言说能力,也即说话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看法。在这本书中,朗西埃把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政治平等问题,从哲学上还原为言说和论辩—这种普遍性的、人类共有的基本能力。换言之,从语言特征及其表达方式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把人类划定为一个共同体。但是,这个看上去齐一的人类共同体,果真是一个内部无差异的感知共同体吗?换言之,形式整一是否就意味着内在齐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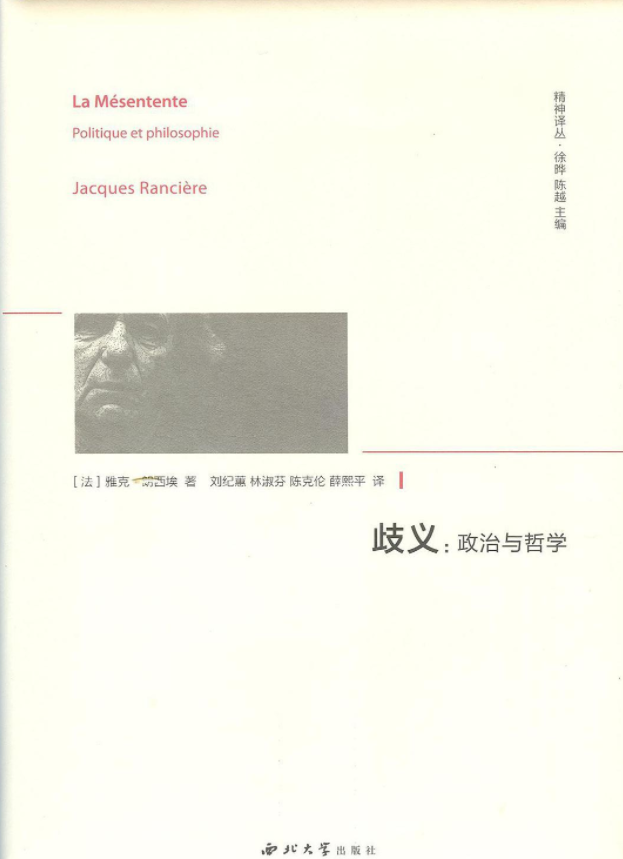
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2015,西北大学出版社,译者: 刘纪蕙 / 林淑芬 / 陈克伦 / 薛熙平.
朗西埃指出,当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把人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性动物的原因归结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时,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区分动物与人类语言能力的不同及其社会属性的差别,但从说话—这种感官知性能力而出发的区分,其实对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尤其是平等原则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因为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描述,在古希腊社会中,相对于城邦公民和自由民而言,奴隶虽然同样能够听懂、理解言说中的语词,并且显然也具备自主地使用语词的感官,但是他们却不能真正地拥有语言。朗西埃分析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要点其实质是在指出,奴隶尽管也具备言说语词的能力,但是他们所表达产生出来的语言却几乎不可能被接受、被倾听或是被理解以及被执行。正是这一点促使朗西埃坚持认为,语词言说这种看似极为普通而又平常的、共同的人类基本感官能力,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种属性的。相反,它常常是具体情境中的一种分裂。
何谓情境化的分裂?分裂就是指例如作为一种被视为是普遍共同种属能力的言说,因为对言说者社会身份阶层的认知和划定,而致使其丧失了它理应具备的同等权利和社会属性。对语词意义的言说,从它自身的表达中被割裂出去。于是朗西埃敏锐地指出:“真正的政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意识到言说与言说本来就是不尽相同的,在于对同一种感性能力意味着什么尚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2](P9)。可见,就此处的论述而言,朗西埃所理解的政治的本原之义,指向的是一种情境化的接受和呈现。在这个情境中,说话被认作是一种人类共有的种属感性能力,尽管言说者的社会身份千差万别,但只要他者表现出了言说的感官能力,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他所言说的语词的意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简言之,我们要接受他者正在言说的这个事实,并且能够、愿意进一步领会并接受其言说内容上的差异及其实在性,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政治才算有了萌芽。
由此可见,在朗西埃的理解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是与、而且也只与“平等”的感性呈现、表达和接受有关。并且朗西埃所说的平等,并不是等着我们去努力追求、有待实现的一个未来性的目标,而它反而直接就是一条在当下延展开来的途径和方法。201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朗西埃指出,在目标、方法与途径的关系中,“并不是目标在决定我们应该沿着走的道路,而是因为方法,它自己向前走的方法,才决定了我们认为可以设想并且达到的目标”[3](P11)。简单地说,平等并不是一个有待达成的目标。它直接就是达成的方法本身,就是我们着手开始的方式。
有鉴于此,在朗西埃看来,当戏剧导演和舞台演员们习惯性地把台下的观众概观、预设为一个整一的感知整体时,这就已经在表演与观看之间挖开了一条鸿沟,观看与表演之间的不平等已经形成。那么是什么东西把剧场里的观众与电视机、银幕前的观众区分开来呢?剧场观众身上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使得他们比在电视前同时观看表演的人更加具有互动需求、更加具有公共性呢?事实是,似乎只要观众聚集在舞台下的座席内,剧场呈现出来的群体主义形式就会被台上的表演直观到,进而把它的影响扩散到舞台的背后。
总而言之,被朗西埃所质疑的核心认知,就是把剧场观众当作感知共同体来看待的历史观点。问题的关键其实也在于这个对剧场观演结构形态的预设和判断,总是跑在演出前面并且贯穿、影响着整个戏剧的进程。但在剧场中,或是在演出面前,其实如同在博物馆里、学校里、街道上一样,只有彼此独自的个人。这些同处一时空里的独立个体,在表演、语言、行动以及他们面前或周围的事物森林中,摸索、探寻着自己的道路。这个作为观众身份的随机性集体,并不直接构成一个齐一的、规整的输入对象。
二、平等的表演:
从课堂到舞台
事实上,正如戏剧理论家们所强调的那样,现当代的导演、剧作家以及表演者也并不是要在舞台上“教”给观众任何东西。实际上,他们如今对戏剧舞台是否要承担教育化角色,是持保留甚至是鄙弃态度的。他们对是否要把教育、教化的目的嵌入舞台表演中,同样也是十分谨慎的。从总体上看,西方的剧作家以及理论家们,主要是想要营造一种有关体验、感知和领悟的表演形式,一种旨在塑造感受力以及行动力的舞台力量。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舞台演出的制造者们仍然习惯性地假设,那些即将被台下观众感受到的或是理解的东西,一定是他们事先放置到、植入剧本或表演中的东西。正是演出与观看的这种单向输入型关系,让朗西埃把戏剧表演舞台与学校里的课堂教学联系到了一起。
朗西埃认为在这种观演观念把持下的剧场舞台是不平等的,因为演出的制造者们预设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平等转化—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均质性。换言之,这其实是把表演呈现与观看行为比作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即观者所收获的恰恰是演出者所呈现和给予的。因而在这个单向、均质化的输入过程中,观众显然已经不被看作是一个主体意义上的感知体,而是变成了一个等待被灌输的空白受众对象。这恰恰就与朗西埃在其教育著作—《无知的大师:关于知识解放的五堂课》—所批判的教学情形极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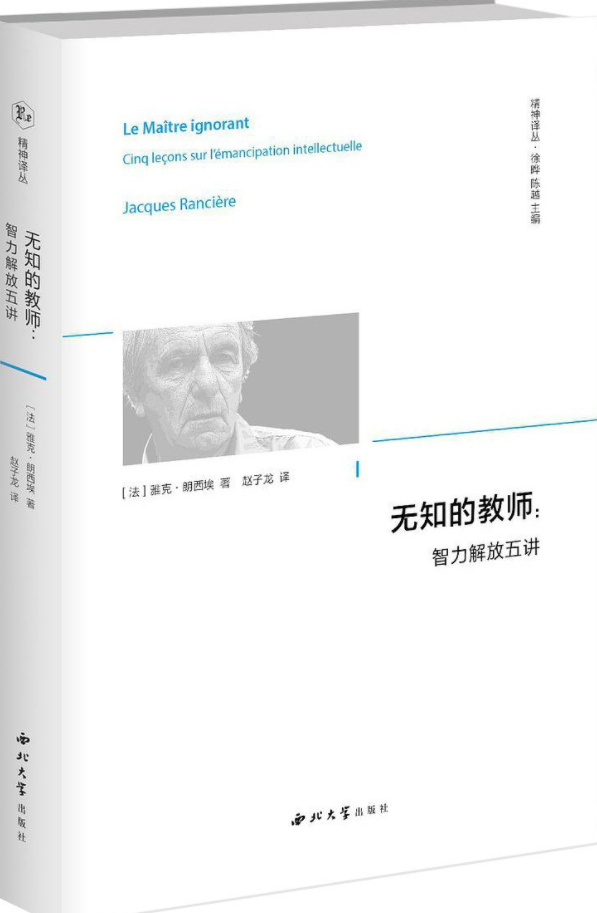
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2020,西北大学出版社,译者:赵子龙.
朗西埃智力教育理论的核心要求是“智性解放”(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这里请注意,不是智力解放。关于智性解放的理论基础—“人人都有平等的智性”,朗西埃分析认为,不同的认知主体在其智力上的外显差异,并不是内在智性意义上的,而只是在运用智力的情感意志力和经验习惯上有所分别。在此基础之上,朗西埃解释说,他所谓的智性平等,并不是说所有人在其智力显现层面上的均质化和齐一化,而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智性能力的类似性、关联性和平等性。那么朗西埃对智性平等的着意强调,就其在教育教学的语境下,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朗西埃看来,智性平等首先就意味着对师生在传统教育情境中存在的、相关结构关系模型(如师生角色的恒定规划、位置地位关系的习惯性对立,有知对向无知、传授对向聆听等等)的质疑和反思。在具体教学活动的语境中,智性平等的目的就是要坚持认为,学生和老师其实都同时既是有知的,又是无知的。这是因为即使是一个如同小学生一般的初学者,他们也终归总还是具有一些基础的语言知识和表达能力,这就可以帮助他们去聆听、观察、记忆、推测老师所讲的新知识、新东西;从另一方面来看,老师虽然对学生的知识盲点以及他自己的讲授计划了然于心,但他对究竟该如何把新知识输送给学生,以期也使他们获得等待被传输的知识则是无法掌控的。
更进一步说,教师其实始终都很难对教学效果、教育过程进行精准的预判和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朗西埃也拒绝认同,在有知与未知之间,存在着一条普遍正确而又绝对有效的传输途径。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知”的老师其实和“未知”的学生一样,他们都需要用自己已知的东西去联系当前的未知。这个运用个体已有的知识或能力,去探寻还未知、不解的知识的过程的背后,正是一种本质上相同的力量—智性。
教育情境下师生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仅仅是体现在“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教师传授、学生聆听”等这些预设性的惯性看法上,其实,它与剧场舞台观演对立关系极其相似的另一点就是,其直接表现在肉眼直观可见的、对物理空间的划分和占有上。如同宏大的剧院一样,学校里的教室虽普普通通,但那同样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在这个整体化的空间结构布局中,存在着两块有明确划分和主权归属的位置区域。这就是由教师所拥有的讲台,以及在讲台下的等待由学生来填满的、虚空的座位。这样的物理空间划分,仿佛就是对知识学习过程及其方法的一种空间化比喻和暗指。因为对所在空间位置归属的划定和分配,远远不止是躯体肉身意义上的,而是直接关系到处于相对应位置之上的师生、观众与演员的实际感知方式和感知方向,也即直接影响到了二者存在、说话和观看的方式。
正是在这个由直观空间分配方式构成的视觉形式中,站在讲台上的教师们最终在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追求中迷失了他们自己。这也如同剧场的先锋改革者所做的那样,在如何沟通、弥合舞台上与舞台下之间的物理空间分配和视觉形式关系时,绞尽脑汁。
在直观物理空间分配方式驱使、支配下的填鸭式、无知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事先预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竭力设计一个有效的、程序化的、准确的知识传输路径和方法。而这个方法的实施过程,实质就像是在对着远处静止的箭靶射箭一般。因为显然教师预设学生将要学到的东西,恰恰就是他自己所正在传授的。“有一边存在着某些东西,在一个头脑或一个身体中—知识、能力、能量—必须被转化到另一边,进入他人的头脑或身体。”[4](P47)由此可见,这个预设性认知的观念,是把本质上原本主要有赖于个体的主动性学习过程(其实也就是主体感性能力的培养、形成与拓展过程),转换成了对一个外来对象的无个性化的接受、储存、记忆与输入。
总而言之,“无知的教师”是在强调,坐在教室台下座位上的,其实是一个个独立的、感知经验和认知习惯各不相同的学生个体。认识到这一点,对教师的教学设计其实具有重要的约束和引导意义。当然,同样重要的则是学生自身对它的领会认知和运用。让我们从教室回到剧院里。既然戏剧编剧、导演和理论家们也早已声明,他们并不想在舞台上“教”给观众任何东西,然而当他们开始琢磨表演应当如何影响观众、演出要达到何种效果时,当他们在时刻悄悄注意着观众的一举一动时,他们的表演其实已经与那些旨在传输和输入的填鸭式教学相差不大了。所以,朗西埃现在要提出的问题和任务就是,戏剧舞台表演必须如同学校教学改革一样,应当要思考究竟该如何走向平等。
把剧场里的观众看成一个共同体,舞台上的导演与演员便也随之构成了另一个共同体,于是演出就成为后者对前者的单向展现和景观性输入。这两个共同体同处一空间之内,但角色、位置、动静行为的区分,最终导致了对观看行为与表演行为的对立性理解。在视觉直观看来,表演与观看的确是一个相对而在的行为过程,因为无论何种剧场,终归是要区分出供演员表演的舞台和供观众就座的座席。然而,舞台上的、有计划的表演行动与座席内的、持续的静坐观赏,尽管在形式样态上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是这个沿袭已久的“被动”的判断,在很大的程度上,或许仅仅是在视觉直观形式上的一个假象。
所以,“剧场应该用故事述说或是写作以及品读的方式(with the telling of a story or the writing and the reading of a book),来质疑自己的临场特权(question its privileging of living presence )并将舞台恢复到一个平等的水平。它应该成为一个新型的平等化舞台(the institution of a new stage of equality),在那里各种不同的表演将被相互理解和转译。事实上,所有的这些表演,它们应该都是把某人所知的联向他还未知的问题。这问题既属于具备表演能力的演出者的,也是在观看行为中的观众的问题。他们共同想要探索发现这些能力,可能在新的语境、情景中,在所有不确定的感知主体中所产生的东西”[1](P12)。
然而,正如对于“无知教师”的教学对象—学生个人来说一样,学生个体必须明白的是,他所要填补或弥合的“无知”,并不是他与教师之间的知识鸿沟,而是他自己已知的和他暂且未知的知识之间的距离。对他来说,那其实是从这一件事物到那一件事物之间的普通距离。既然如此,台下的观众就一定要等量接受台上演出的目的和主旨吗?戏剧制造者们越是要努力表达和输入,越是对平等舞台的偏离。
所以,在一个具有真正平等观演关系的戏剧舞台空间里,舞台表演的目的就在于把观众引导、塑造成对演出景观的主动感知者和诠释者,并且通过观看表演来联结他们自己的感知经验,进行他们自己的转译、理解和体悟。简言之,观众观看表演并且勾连、对比舞台上的可能和他们自己有所关联的故事,并最终从中构思、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新故事。
三、观看的观众:
从剧场“歧感”到审美行动
“我们的表演必须所要经受的考验—无论这种表演是教学式的还是舞台上的,言说的、写作的后者艺术创作的—并不是要展现某一个集合体的倾覆性能量,而是要去容纳显现其中每一个无名者的个体潜能(is not the capacity of aggregation of a collective but the capacity of the anonymous),是使每一个人都能与他者平等的能力(the capacity that makes anybody equal to everybody)。这个能力则必须通过不可预测且不可缩减的空间距离(unpredictable and irreducible distances)产生作用。”[1](P12)
这说明,表演和观看尽管在直观形式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依存状态,但在它们之间其实还有一个隐蔽的环境结构元素,这就是剧场空间本身。剧场空间虽然在物理形态上,需要对供演员表演的区域和供观众就座观看的区域作出界限化的区分,但是这个区分始终只具有视觉形式上的意义。在这个界限明确的物理空间分配背后,其实则是舞台演出和观赏观众之间,通过以表演为中介而交织的内在无限心理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不断交错、叠加、冲击、融合、前进与后退的、混合着思考与情感的氛围体。现在问题的微妙与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混合空间的存续又始终必须以在表演与观看、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实际物理距离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的距离不仅不能被无限地压缩,反而需要对其进行适度的保留并加以小心地维护。
前文已经指出,剧场观众虽然在视觉直观上构成了一个形式化的、整一性群体,但是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其不可撼动的宗旨和统一准则。因为它其实指向的是“一个由诸多不同种类的感觉而构成的数量结合体:形式、语言、空间、情感等等。因而它实际涉及的是不同‘意义’的感觉的结合”[1](P57)。比如说下面这样的一种社会场景:巴黎郊区的某个区域的全部市民,将自己的政治要求、口号印制在统一的黑色T恤衫上。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共同的姿态,并在摄像头面前被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一个直观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其实是由各个单个的市民杂合、并存而成的“共同体”。这时候我们之所以要称之为一个“共同体”,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被直观到的形式而已,而这几乎只是视觉意义上的。如果站在平等人格和审美解放的立场上,我们就应该要透过这个形式化的整体,看到其中每个构成性的个体,并对其个体化的感知和需求进行识别、发现和承认。换言之,在审美感知的视角下,这个共同体的实质意义和在场目的并非是为了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而在于他们之中的每个个体都共同地通过直观形式展现出了对自身之“歧感”(dissensus)的体会和诉求。
那么“歧感”到底是什么?朗西埃解释说:“在最抽象的层面上,‘歧感’意味着感知与感知之间的差异:一种同中之异,一种对立面之同。”[5](P205)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差异主要不是指不同个体在身份、地位、工作、意见等社会学意义的外显差异,而其实是指A感觉秩序与B感觉秩序之间的不同,以及他们的对向性和同时性的存在。
戏剧一般都是在剧场中上演,剧场实际上则是一个由剧场建筑、舞台、表演和观看行为构成的艺术世界。而在整个西方戏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动”似乎一直就是坐在座位上的观众甩不掉的标签,甚至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没有观众,就没有剧场”的惯性认知和剧场共识。而当舞台下座位上的虚空一个一个地被填补,空虚的位置慢慢地越来越少,直到整个的就坐区域被覆盖,这个时候一个终于能够让剧场和舞台同时满意的对象,一个其自身获得完满性的概念—观众,才算真正地得以呈现,并迅速地被舞台和演出接受,继而整体性地被纳入为它的演出对象和演出目的,成为等待观看的共同体。
然而,朗西埃始终坚持认为所谓的“政治共同体”,“早已经是一个歧论纷争的领域”[6](P34)。这或许从他1989年把自己研究工人解放的著作标题定为《无产阶级之夜》(The Night of the Proletarians,英语译为《劳工之夜》,The Nights of Labor)①的命名方式中,就可见一斑。朗西埃在书中认为,工人们被习惯性地定位为没有时间、不应该到工厂、车间之外的其他空间去的人。因而,一旦工人在傍晚、夜间走出车间、宿舍、休息室,一旦工人也如同资产阶级一样去散步、谈话、聚会,政治便由此产生。
同为欧洲左翼思想家的齐泽克,在《劳工之夜》这本书的后记中如是评论,“作为欧洲民主左派的一员,朗西埃的学术理念主要是基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著名口号—‘自由是那些想法不一样的人的自由’的坚定信条”[7](P34)。
那么,这样一来,朗西埃就把对“政治共同体”的质疑和反对,自然地延伸到了对观众整体这个概念的反思上。需要特别明确地是,这个反思是直接针对戏剧导演和表演策划者而言,因为观众是对他们而言的共同体,而不是观众自身的属性化状态,他/她还是他自己。既然“政治是一种歧感形式,这意味着你不能从任何一种共同体的本质来推断它”[2](P9),那么戏剧家和演员们就也不能够直接以观众整体为对象去策划表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共同体式的整体化界定和预设,是不平等的,是非政治和非美学的。
读者们或许早已非常明显地察觉到,朗西埃对剧场和戏剧所持有的观众观念的反思,其实赋予了单纯的艺术观赏行为,以所谓平等和自由为主要口号的浓烈政治意味。甚至说那是一种强加,也似乎并不为过。但是透过法国评论家哈兹米格·科西彦(Razmig Keucheyan)的分析和观点—“在朗西埃那里,一种美学意义的感知形式,构成了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8](P35),我们或许也能窥探到作为西方平等政治哲学家出身的朗西埃,反对戏剧和剧场持有观众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目的,其实在意图是为观众自身的审美空间和自由行动保留一种可能性。
因为在观众共同体观念的背后,其实所涉及的就是朗西埃所反复强调的“感觉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问题。即是说,在戏剧和舞台演出把台下的观众视作一个感知共同体时,这就完成了对感觉的一种分配,对剧场内感知结构的形态化划分。这样的划分直接导致了戏剧和剧场对观演关系的框定,进而影响了戏剧和舞台演出的策划和进程。换句话说,朗西埃《被解放的观众》的核心目的并不是要去质疑剧场表演和改革方式,他关注的焦点是为什么戏剧导演和理论家总是要不自觉地把观看行为和表演行为对立起来。
或许我们也已察觉,朗西埃真正的箭靶子其实是舞台上和舞台后的预设性认知,而不是在舞台下。这样一来,通过对诸如共同体观念的反驳,朗西埃就为舞台下的观众捍卫了、预留了他们自己的感性空间,进而就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审美理解和行动方式。直觉上看,他的用意似乎是要去保护观众的个体感知空间,鼓励观众个体在自身感知经验和感知倾向的基础上,直接去面向舞台上的一切。不难推测的是,之所以要如此捍卫观众的感知权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平等政治哲学和他对剧场审美空间的平等政治化解读。
概而言之,朗西埃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希望观众的感知和反应是来自于舞台上的安排和规划,而应该来源于每一个认真观看的观众自身。如此来看,朗西埃是为剧场里的观众,在理论层面上争得了自主性的发言权、感知权和行动方式的权利,但至于具体到每一个观看的观众身上,他/她究竟能否把握和展现这些权利,则是他未能回答的。或许,朗西埃志在追求的不是观众或观看行为的本质,而只是在为观众群体的主体化剔除历史性的理论障碍。换言之,朗西埃的启示或许是,对于我们当中每一个前往剧场的观众来说,所担负的任务和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是,我自己如何通过他者(舞台表演者)眼中的观看行为,而自证成为一个客体性的主体感知者。
四、结语:
观看者的审美空间
总体来看,朗西埃认为,在近代西方以布莱希特和阿尔托为分别代表的戏剧剧场改革理论和行动中,他们的初衷和目的几乎都可以简缩为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需要一个新剧场,一个不能只是观看或取消观看行为的剧场”[1](P3)。因为即使只是从戏剧的概念源头上来看,早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戏剧本就意味着模仿和行动。
于是乎,既然观众的行动表现与否系于舞台上的表演,因此剧场和舞台就需要具备一种动能。因为正是通过演出者传递出来的动作、激情和精神,观众才能转静为动,他们的行动才被激发、被点燃。无论是观演边界的模糊,还是角色的调换,这个让戏剧家执迷的可谓是一种“超剧场”[9](P45),因为它试图通过把舞台表现转变为生活的在场和主体的临场,以求唤起被视作为感知共同体的观众整体的同步感知。
是的,剧作家、导演和表演策划者们当然有着他们自己试图要述说的故事、呈现的图景和传达的意义。但是,如果他们执迷于在相关的实现方式和表达手段上,继续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摸索以何种方法向观众输送、暗示、指引,以求稳当、精确而又均质地把舞台上的图景和意义输入到舞台下的观众感知中去,那将导致不平等的剧场。那样的舞台演出,其实质则是表演对观看的强制。因为如果要求把表演呈现与观看获得,完全等量、等节奏地等同起来,这同愚化观众又有什么分别呢?
观众在座位中的注视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被动,尤其是当他/她正积极地用自己的感知方式和感知经验,把心灵与舞台表演相关联时。正如英国学者阿尔塔·诺弗尔(Aletta Norval)(以下简称诺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在剧场里就座着的、静静地观看演出的观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她自己内在的心灵言说被感知、被体悟到的可能性”[10](P34)。这就表明,面向舞台演出的注视和观看,其实是一个主体化的显现过程。如果戏剧家们把在舞台上对静止观看行为的忧虑,替换成了对为达到预期的演出观看效应的千方百计的追求,那实质就构成了一种越界的强制。因为,即使观众在外在形式上表现出了舞台所期待的对演出的同步感知,但实际上观看行为只有通过对舞台的适时后退,才能够使行为主体自身得以显现。观众也是在对剧场的疏离当中,才能察觉到自身感知活动的动因和结构。
当然,关于观看行为的感知结构的理解其实还是十分模糊和不确定的,同时这也不应是剧场就此可以轻视、忽略台下观众反应的理由。剧场空间的封闭内向性存在,已经在客观心理认知上促成了舞台上下的交融一体。朗西埃对舞台上和舞台背后的观众观念的批判,也是以其轻视舞台下的现场反应的实际作用力和影响力为代价的。诺弗尔以及尼古拉斯·康普瑞德斯(Nikolas Kompridis)也都曾对朗西埃理论中的这种缺乏接受性、不重视反应或缺乏反应的思想进行了近似的批判[11](P8)。因为众所周知的是,观众任何类型的反应,不论是何种声音、表情、肢体动作还是观众的凝神屏气,其实都是在与舞台上的演出互动,甚至牵引着它的进程。
综上所论,朗西埃平等剧场和歧感感知论的根本要点其实是,作为个体的观众虽身在剧场空间结构之内、并且以在固定座位里落座的方式进入到了观演关系的模式中,但这并不是说他/她就必须按部就班地跟随舞台演出者和导演们所预先制定的感知分配节奏和反应方式。无论这个观点对戏剧导演和舞台演出提出了多么大、听上去也多少有些偏狭的质疑和挑战,它为每一个观看行为的主体—观众—所捍卫的感知自由和思想空间,却仍然是颇具有审美教育和自我认知的意义。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对于走进剧场的人来说,他/她能否在观赏活动中同时注视到舞台和他/她自身,能否成为一名真正的、在观看着的主体—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主体在场”,则是需要他/她自己去认真对待和用心体悟的。在静观状态中进行的注视行为,虽然被限制了其所能够发挥的休闲消遣功能与日常娱乐性,却也被赋予了巨大的、如何通过注视行为而使主体自身得以显现的审美使命。应该也是在这个意义下,那些被希望跟随呈现表演动能的观众们,显然也需要一座克制而他者化的剧场。
本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仅做分享使用,不做商业用途,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留言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责编:柳眠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内容由数艺网主动采集收录,信息来源为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公开网络发布内容。第三方如需转载本内容,必须完整标注原作者信息及 “来源:数艺网”,严禁擅自篡改、删减或未标注来源转载。 并附上本页链接: 若您的内容不希望被数艺网收录,或认为此举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敬请通过微信 ID:d-arts-cn 联系数艺网。我们将致以诚挚歉意,并第一时间为您办理下架或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