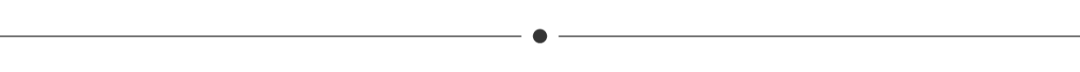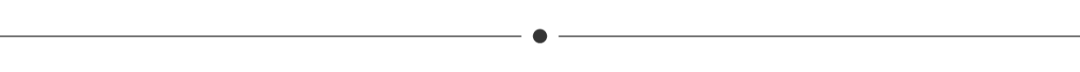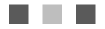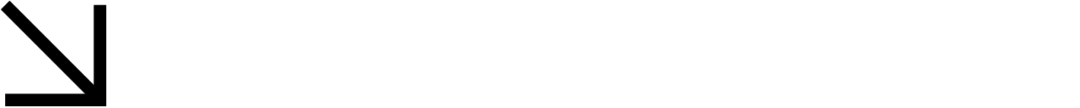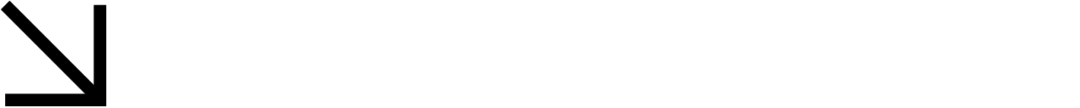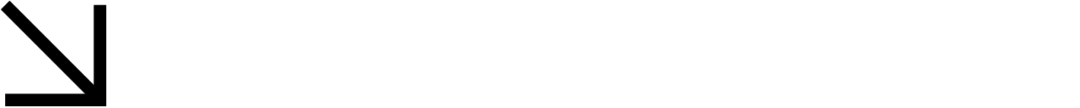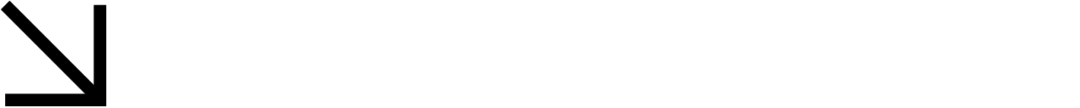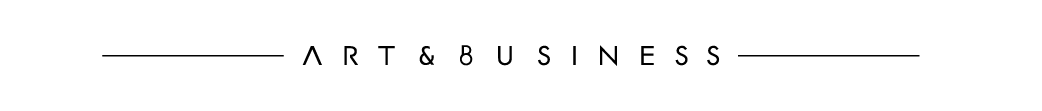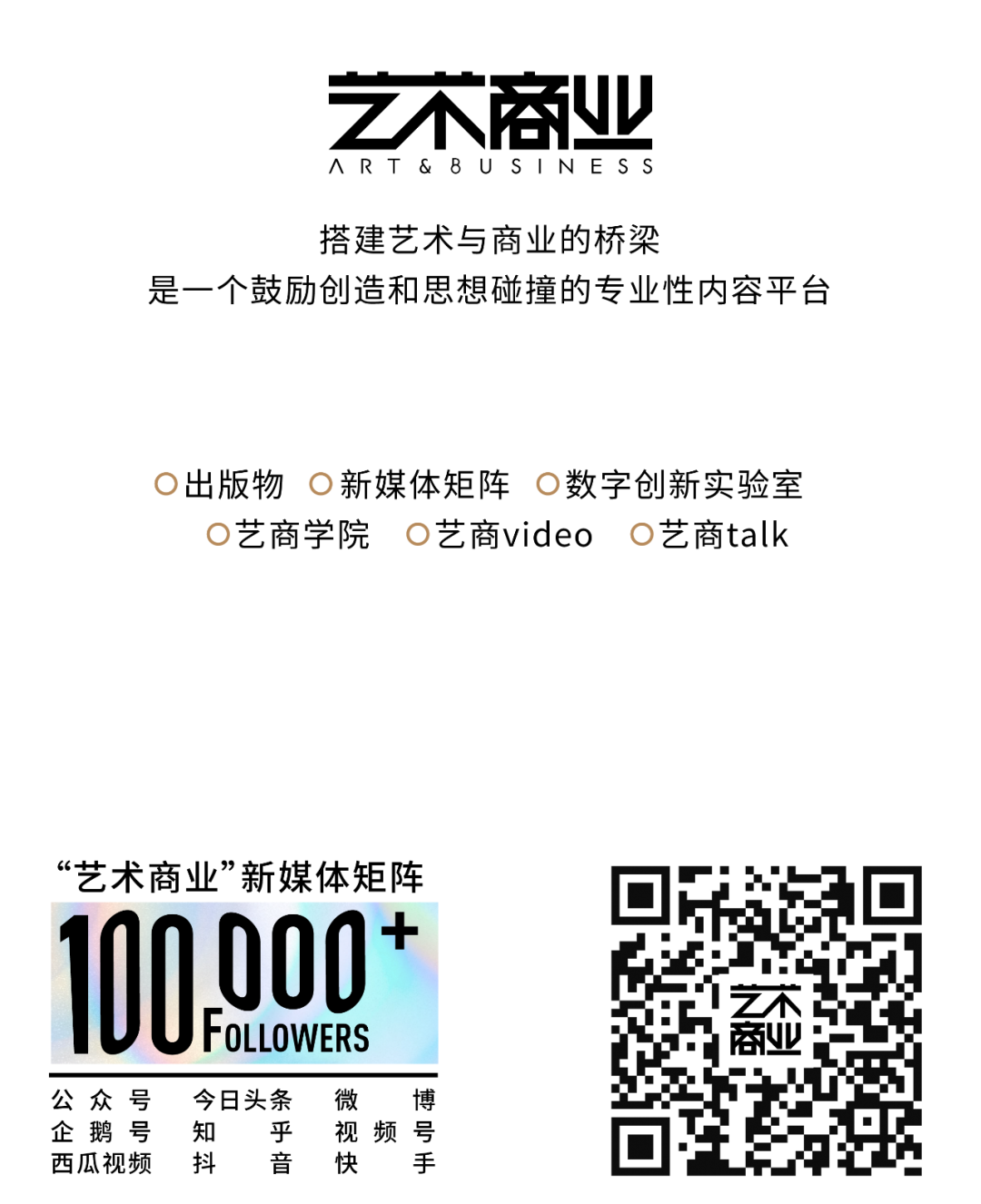柏林墙倒塌的那年,杨洋去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留学读书,刚进校时苏联还是苏联,进校第二年苏联就解体成了独联体。在历史剧变漩涡的杨洋那时处在自己骄傲的青春里,画画、拿奖学金、穿漂亮衣服、旅行、交朋友、谈恋爱,社会的潦倒阻挡不住一个年轻人的野蛮生长乃至生机勃勃。这些翻天覆地的场景却似乎没在杨洋的绘画作品里留下痕迹,她的画是女孩、动物、树、小花,好像与丑陋的现实无关。张爱玲说:“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以及你爱过的人”。其实她历经的悲伤与幸福、她想表达又难以说清的一些感受,那些现实沧桑全都藏在里面了。
采访时,杨洋跟我们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她留学苏联时一个塞尔维亚的男性朋友的遭遇。朋友是特种兵,20几岁的年纪,是在南斯拉夫解体时经历过浴血奋战的人。有一次小分队去敌方执行任务,是一个村庄,要干掉敌方的狙击手。一人站一个点往前走,进了一个老房子,老房子是巴尔干地区常见的房子,带地窖。他们走进地窖,用手电照了一下,当看到里面的场景时,所有人立刻紧张得背对背靠在一起,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地窖里是齐膝深的血水,惨烈得可怕。这个地方得杀了多少人呢?军人都有直觉,从直觉来讲这个地方应该没有敌人。有人舔了一下——虚惊一场,不是血水,是红酒,是地窖里的酒桶碎了,淌出来半地窖的酒。欧洲人嗜酒,几个人便开喝。喝到不省人事,第二天太阳出来,所有人醒来,看看四周,恍若隔世,然后恐惧袭来,都觉得后怕,抱头痛哭。如果真有敌人过来,一梭子子弹这些人就都死了。都是命大。
美院同学的课余聚会,苏联香槟配大香肠(杨洋说,一直没觉得俄罗斯香肠好吃)
杨洋那时二十三四岁,和她的同学听这个故事时像听段子,里面没有杀人,只有生死之间的细节,不能细想,否则后脊梁是发凉的。都是差不多同龄人,对世界充满幻想和期待,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沉重。杨洋那时意识到,生活可能会在幽默、搞笑和生死之间随意切换。杨洋人生中有6年时间在莫斯科留学,留学本身不仅仅是你去了一个地方,学习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她所体验到的点滴,不只是她人生里付诸一笑的花絮,是塑造了一个人对世界的敬畏与认知,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些经历与认知,同样塑造了杨洋的艺术世界。1989年杨洋公派去到苏联之前,对那里的想象来源于苏联留学归来的师长的转述里。没有网络的时代,年轻人对世界无法认知,把局部的描述当成全部。杨洋记得附中开party时同班同学穿着绣着花边、泡泡袖的苏联民族服装,相当惊艳,那是同学的妈妈五十年代留苏时带回来的。阳光灿烂、朝气蓬勃,有好看的衣服,天天开party,这些是杨洋认为的留学生活。直到她坐了八九个小时的飞机,抵达莫斯科的机场,她发现11月的莫斯科整个色调是暗的。在杨洋待过的六年时间、经历过的三个季节里,苏联在她的印象中都是“暗的”。莫斯科大学预科宿舍的小聚会
那一年中国一共向苏联派出了数量前所未有的80名留学生,分别来自全国不同领域的高校,其中央美和浙美的美术生有9人。这些人懵懵懂懂地来,懵懵懂懂地被分配在不同的学校。杨洋在莫斯科大学预科学习了俄语,1990年通过了专业考试进入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绘画系。苏联有两大美院:列宾美术学院和国立苏里科夫美院。论历史和名气,列宾美术学院比苏里科夫更胜一筹。列宾美院1757年便成立,原是俄罗斯皇家美术学院,位于涅瓦河边,学院图书馆里藏有纸本的丢勒原作令杨洋羡慕不已。杨洋最初毋庸置疑地选择的是列宾美院,为此特地去了一趟学校,而后改变了主意。列宾标榜一种传统,画风在杨洋看来近乎刻板:在画布上画一个坐着的人像,人物的头有多大,上面留多大空间,下面留多大空间……限定得非常细致。“我最痛恨的就是,画室里10个人在画画,你分不清谁是谁画的。他们标榜这是传统,我认为这是教条。”苏里科夫美院位于莫斯科。1939年格拉巴利创立了莫斯科国立美院,1948年以俄罗斯著名画家苏里科夫命名。在实施教学计划过程中,以教授指导和个人工作室为主。这些教授大部分是有名的艺术家,大多数是美术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风格相对当代,允许学生做各种不同的尝试,“只看你画得好不好,不看你画成什么风格。”杨洋选了苏里科夫,一是这种宽松,二是在莫斯科上了一年预科,她清楚首都和外省的区别。莫斯科各种国家级展览、国际间交流展、音乐会和芭蕾舞演出,街头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和苏联各民族的人们,书店和唱片店中各种画册书籍和音乐,对于大学时期的学生实在是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有句话这样说,“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地方是两个国家”。某画室里的同学聚会(应该是版画系的工作室),尾声阶段,酒瓶空了,沙拉盆也见底了

在苏联功勋雕塑家慕希娜(就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片头雕塑的作者)的家中聚会。慕希娜的家在莫斯科慕希娜广场边,国家配给的独栋小楼分住宅和工作室两个部分,随处都是慕希娜生前做的小泥塑(相当于手稿)。杨洋(中间)身边的男生是慕希娜的外孙,也在苏里科夫学院上学,艺术世家出身,算是学生中的贵族
苏里科夫美院学制是本硕连读六年,加上预科一共7年。7年的留学时间对杨洋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来说无比漫长,让人感觉一辈子都要待在这里了。苏联美术教育体系和央美非常接近,因为原本新中国建国后的美术体系就是承袭苏联。1990年杨洋进入苏里科夫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依然发现了很多差别:苏里科夫美院的画室面积更大,所以每个学生的绘画空间就更充裕,选择视角更多。每组模特摆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并没有严格的课时要求,比如,80课时的模特,是要求课堂作业在80课时内完成,至于最终画30课时还是80课时,由学生自己决定。我属于手比较快的学生,又很少翘课,所以经常在其他同学画一张画的课时中,我画出了一大一小两张画。油画作品《莲娜》,就是画完模特正面全身像后另寻角度即兴画的一幅小画,反而因为光线和视角独特,成为一幅没有课堂作业气的完整作品。
苏里科夫的油画专业和壁画专业都在绘画系里,绘画系着重于“绘”的概念,区分于版画系的“印”和雕塑系的“塑”。我后来选择的画室是绘画系纪念性绘画专业,所学课程除了油画技法,还有干壁画、湿壁画等古典壁画手法。有一阵颇为迷恋干湿壁画的材质效果,遇到一位颇有贵族气质的美术史专业女生,觉得她的形象气质与古典壁画的美颇为契合,于是创作了油画作品《丽萨》,基底效果就模仿了干壁画的粗糙感。

Lena,1993
布面油画,55x46cm
杨洋还能记得美院有一类模特非常独特,最后一抹风景线在刚入美院第一年被她看到,二年级就没再看到。1990年苏联有一部电影叫《国际女郎》,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特别漂亮的年轻女孩子,高级妓女、交际花,她们周旋于权贵、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之间,高昂的“交际费”甚至可能达到5000美金一晚(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5000美元)。但苏联那时要求所有公民必须有工作,没有工作是不被允许的。那些姑娘们需要找一份闲差,有些人就在美院当模特。“我见过她们出入美院,但班里没有分到过这么好看的模特。”杨洋说,“俄国姑娘的好看率太高了,令人发指的高。身材好,气质好,又会打扮。这样的姑娘都有豪车接送,都穿着高跟鞋、貂皮大衣。一身进口名牌。”在苏联留学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亚非拉三个地方,没有种族歧视,像一个大家庭。真正的鄙视链看的不是人种,是才华。通过央美的训练遴选出来的人,在苏联都能排得上优秀。“非洲同学和南美同学画得最差,东欧同学不太重视写实功底。”杨洋去了之后门门高分,年年有奖学金。中国公派的留学生,奖学金发的都是美元,在当时苏联解体卢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占了汇率很大的便宜,生活可说很优越。杨洋与俄罗斯和美国艺术家在一起,1994

宿舍外的投币公用电话,左侧女孩是韩国与俄罗斯建交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生杨洋2016年画过一幅油画《1990》,黑发垂肩的女孩站在树荫中,望着远方的喷泉和金色雕像,那是苏联国民经济展览馆,一个过去的时代。女孩的手里拿着一张黑胶唱片,封套上写着四个字母 KINO。
杨洋《1990》, 2016 ,布面油画,110x110cm
这张黑胶唱片是1990年21岁的杨洋在莫斯科的唱片店里买的,花了高于普通唱片10倍的价格,是原苏联时期著名摇滚歌手和青年偶像维克多·崔的绝唱“黑色专辑”。“我并不知道我手中的这张唱片代表着什么。只是一种直觉,那些我当时听不懂的歌中有一种心底的力量,属于我,属于跟我一样站在那个历史转折点的青年。”全黑的封面只印着简单的四个字母KINO(崔的乐队名称,俄语“电影、影片、电影院”之意)。封套纸张粗糙,印刷简陋,封底的乐队成员照片对版不齐。维克多·崔因车祸死于1990年,但出版这张专辑时并未预见自己的死亡。这张专辑仿佛暗示了他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宿命。1991年苏联解体时杨洋并未注意到周围有太多的变化,她认为“之前就是不好的,解体是顺势而为。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崩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不相信国家会终结在自己手里,还相信在1989年他能度过“危机的顶点”,但其实国民生活水平已经很糟糕了。“货币发行增长,卢布购买力不断下降,日用品和服务业的价格继续增长……老百姓发现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商品越来越少,于是开始囤积各种各样的商品。不仅食品商店,就连首饰商店一大早都排起了长队。”(《苏联的最后一年》)“1991年以后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我出门一般带5美元现金,看到前面肉店有人排队,卖大块带骨的牛肉,你要算算排队的人和肉的数量,估计排到最后能买到,就跟队尾的人说我一会儿来排队,就排你后边。肉店附近100米之内肯定有换钱的,跑过去换2美元的卢布。一块牛肉两三公斤没有多少钱,2美元花不完,买了肉以后提着再往前走,遇到其他东西再买。通常我一周出去一次,带5-10美元,回来的时候东西就拿不动了,会剩点钱打个顺风车。”
那个时期苏联人的服装、面部表情都是沉重的。美院外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线地铁站,有一个大食品超市,通常她进去时已经没有可以买的东西,只有一直整齐地满满码在某些货架上的几种罐头,而那些罐头一定不会有人买,因为太难吃。超市门口会有20几个老太太站成一排卖面包——清早时老太太们在面包刚出炉的时候买一些,白天再以稍高一点的价格卖出去,赚取一点生活费。这些为国家干了一辈子的老人是制度崩溃最直接的受害者,退休金变成很小的数字,财富一洗而空。青春和力气不在,年老的人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苏里科夫美院的二人宿舍,虽然很乱,但是有鲜花和电视
在杨洋的印象中,苏联的匮乏并非人民衣衫褴褛沿街乞讨,只是缺乏现金流。苏联人的房子都有现代化配置,充足的集中供暖和水电,有冰箱、彩电,很多家庭有汽车,郊外有消夏别墅——就是自己的一块不大的土地,房子自己建造。杨洋所在的大学宿舍一个双房套间住四个学生,家俱寝具都是学院提供,统一的白色床单被罩都是上过浆、熨好的,叠得整整齐齐,定期更换。这是俄国人的标准生活状态。在国家剧变的时候,苏联仍给旅居在这里的外国人以光鲜的外表。
莫斯科第一家麦当劳,1990

“身后是莫斯科人排大队等候进入麦当劳,方形的大广场排了一圈半,我们几个中国学生一起去排了两个小时才进去,吃到了热乎乎的炸薯条和麦香鱼。当年的麦香鱼用的鳕鱼新鲜美味,配上充足的酸黄瓜沙拉酱,非常好吃,至今难忘。”杨洋说
因为假期够长,在苏联解体之前,杨洋游历过后来独立出去的白俄罗斯、中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她发现一个规律,苏联各民族性的差异和文明程度在地域上有所区分,“越往西越文明,往西到白俄罗斯,人的外貌、气质、穿衣打扮,就感觉要比俄罗斯还要更优雅一点。再往西是波兰,波兰人又比白俄罗斯人还要更好一点。往东到了中亚,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能说不文明,当地人热情质朴,但就是不按规矩排队,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 在莫斯科有一个机场专门飞中亚,没有廊桥,步行走到飞机再登机。杨洋有一次去布哈拉,看到挤在舷梯边的人群中有一位中亚老大爷,手里提着一个笼子,里面是一只公鸡。杨洋明白了,在苏联,飞机就像长途汽车,机次频繁票价便宜,像中国人赶集坐车,乘客们带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行李。
布哈拉,1991

撒马尔罕,1991
杨洋去东欧时柏林墙已经倒塌,因为拿公务护照,东欧国家和西柏林都免签进入。西柏林像是一扇小窗户,让21岁的杨洋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真正模样。东西柏林一墙之隔,差距极大。不论是城市还是人的精神面貌,对待如杨洋这样的游客态度有极大的反差。杨洋那时想,富裕真好,富裕了人都很nice。杨洋第一次去东西柏林的时候墙刚刚拆,第二次去东西柏林就已经合并。那时整个东欧都在闹新纳粹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光头党盛行,以消灭外族人为宗旨,只要见到亚洲人就袭击,没有任何缘由。东欧和苏联的公派留学生有一个自己的通信网络,大家会互相告诫。杨洋还是在东柏林被袭击了。柏林,1990夏
柏林,1990秋
当时杨洋和同学站在地铁扶梯中上行,右侧下行的扶梯中跑下来三个光头党,头发剃得非常短,衣着有些重金属,和普通人不一样。只是一闪而过,杨洋突然眼睛刺痛,立刻看不见东西,眼泪哗哗流。光头党对着杨洋的眼睛喷了瓦斯。
那一瞬间杨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很可怕,因为眼睛是画家最宝贵的东西。但她有个优点,遇事不慌,上楼之后让同伴找到车站医务室。医生没多问,迅速给杨洋清洗眼睛。“可见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我很幸运,因为爱美,我白天是戴隐形眼镜的。催泪瓦斯没有直接伤害角膜,不然那么近距离的攻击,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东欧,1990
保加利亚的深山修道院
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船
布达佩斯
在外游历,少不了这些多舛的遭遇,更多是不同世界不同文化带来的多元刺激,比如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雅致、苍凉,仿佛千年历史就在眼前;比如匈牙利对色情杂志的坦然,让杨洋感受到一种自由的心态;以及当时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对身体的一种开放态度…… 后来杨洋回忆起这些时写道:比起巡回画派和东正教圣像画,这种相对多元化的视觉刺激对我艺术趣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面对冬宫中丰富的西欧大师作品,俄罗斯大师列宾特展中从盛年到晚年的几乎所有作品,我能清晰地看到,俄罗斯绘画大师和苏联众多优秀画家的传承和来源与西欧的艺术其实一脉相承。这一时期的认识和思考,使我明白个人风格的形成应基于对传统美学和绘画实践的融会贯通,而不是遵循某一流派的笔法和教条。
毕业生独立画室,2人一间,毕业生经常会很默契地轮流独用画室。杨洋和一位埃塞俄比亚六年级男生共用一间,她一般连续画两天一夜(吃睡在画室),然后回家一天苏里科夫有个规定,允许全优生提前一年毕业,前提是在五年级同时完成所有课程和国家考试,以及毕业创作与答辩。杨洋从入学时一直保持全优成绩,她衡量了一下工作量,向院方提出了提前毕业的申请。1994年秋天到1995年夏初便成了杨洋留学生活最紧张的两个学期。杨洋全身心投入创作让她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正是这个时期,她创作出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坐着的玛丽亚》、《玛莎》几幅探索性的作品。其中《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作为杨洋的毕业创作作品在答辩中获得教授们的一致好评,获得满分5分。“相比几乎是导师指定题材的《春之漫步》,同期创作的《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坐着的玛利亚》是我自己更得意的作品,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探索的薄画法,使颜料呈现流动性,突出线条和笔触在情绪表达上的作用,使画面在突出庄重深沉的内心情感的同时,不失轻灵的透气感。至此,我留学多年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对各种技法的试练,对自我风格的探索,使我从一个对艺术初窥门径的起点,走上一条通往真正艺术探索的专业道路。”杨洋1995年从苏里科夫美院毕业,但她的毕业证书上仍然印着CCCP(苏联)的字样。
杨洋《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Divine and Earthly Love, 1995
布面油画,146x114cm
杨洋现在觉得庆幸,六年最美好的时间如此丰富多彩、惊心动魄地度过,多少有些不枉过青春的感觉。但当看到杨洋现在的作品,总是卡哇伊的主角,与她个人经历和年龄的反差巨大。“很多人甚至以为我是90后”。“所有人都喜欢萌萌的东西,小孩、小狗、小猫……这些可爱和美好,包括青春,就是生命的基础,是值得赞美的东西。这个题材与年龄无关。因为留学,我是同代人里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接触动漫最多的。当时苏联的国家台里播放着全盘端过来的西方节目。1992年之后,莫斯科的录像带租赁业务很普遍。俄国人翻制的美国影片录像带有一个好处,不用字幕,是口译,会有一个音轨全程口译。我是半路学的俄语,读写不好,但听力还行。那时我喜欢租的是动画片,各种动画片,像迪士尼新出的《美女与野兽》,我都是第一时间看到。”但罗马不是一步跨过来的,从苏联的杨洋到现在的杨洋,中间历经了无数的嬗变。回国最开始的几年里,当她重新生活在四季分明、阳光灿烂中时,有了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冲动。她抛开模特和素材,完全依靠想象来塑造人物和场景。“唯一令我遗憾的是,27岁的我还不能很好地驾驭大画面里的所有细节,多年在高纬度生活导致的色彩趋于深暗的惯性,也要过将近一年才能彻底改观。”
杨洋《命题游戏》
A Game with Themes,2000
丝网版画, 73x56cm,印数:75
1997年儿子出生后,杨洋难以有大块连续的时间进行深入集中的油画创作,于是将重心转到丝网版画和实验水墨。在1998年到2014年期间,杨洋拥有国内最先进的私人版画工作室,丝网版画创作条件非常得天独厚。这期间杨洋创作的《命题游戏》,探索了丝网版画的一个极限:精细度。这幅作品中,杨洋用了几十版颜色实现画面丰富的色彩变化。画面构图以单色背景为远景,装饰性拱顶和树叶花样为中景,突出了作为前景的中心人物和扑克牌。《命题游戏》成为杨洋早期版画的代表性作品,后来入选了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展。2005年,杨洋在创作完《锡耶纳之窗》等版画后,对丝网版画表现形式的探索告一段落。在杨洋看来,2006年的四联油画《四个小女神》是她艺术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她在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的杨洋,经历了伴随孩子的成长以及自我成长的十年,无论是精神还是能力,已经到了一个嬗变的瞬间。这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幅画中小女孩纯真又复杂的面容上。
杨洋组画《四个小女神》(局部),布面油画,2006
到2015年之后,杨洋创作的画面进入了另外一种样貌:越来越少的元素,越来越单纯的背景。“在《夕阳中的旋转木马》中,我开始由繁入简,在油画的创作中抛开物像的客观细节,转而专注于我创造出的另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相似的外形,但是更纯粹,省略了现实世界那些琐碎的细节,以及那些细节传达出的与画面情感无关的信息。” Carousel in Dusk,2016
布面油画,105x100cm
如今,杨洋的画面不断精简,纯净,取材上更钟情于童话题材。样貌是卡通的,内核却是现实的。这种看似单纯甜美的画面,却对观者的触动很大。这是杨洋惊喜的一个发现。她通常与画中的人物是共情的,“我读那些书,我去观察,我去交朋友……我生活的很多细节都灌注到这个人里面了,有很多我想表达但说不清楚的东西。如果我所了解的历史沧桑感能用文章写出来,如果组成悲伤的那些因素可以用语言清晰地描述,那我或许就不需要用画画来表达了。”如今,世界又出现了战争和分离,这些注定又在影响着艺术的面貌。在杨洋的最新油画作品《森林中的小红帽》中,女主人公穿着朱红色的兜帽披风,披风中露出大红丝绒的曳地长裙。她独自走在黑暗森林中,一只手提着精巧的小皮箱,另一只手抓紧兜帽披风的领口,圆圆的脸上只有两只眼神复杂的大眼睛,看着画面外的世界,带着不安和疑问。Little Red Riding Hood in Forest, 2021
布面油画,130x13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