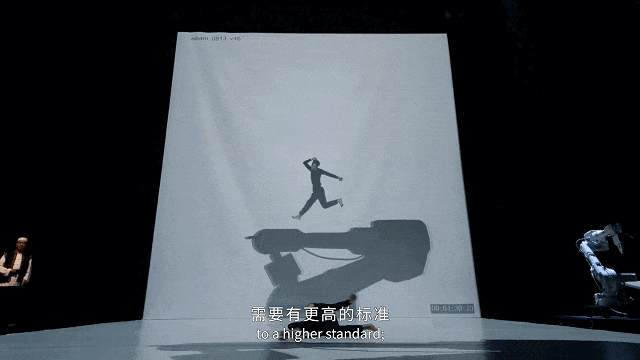李建军导演新作《变形记》于阿那亚戏剧节上演,他在剧场中重构了卡夫卡的文本,将原著中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替换为中国快递员,这种创作方式已然取得成功,然而正是这过分的“恰当”削弱了剧场艺术的力量。作品外观被精心打磨过,最粗糙的棱角却被磨蚀了,成为文学,成为娱乐,成为景观。李建军导演的话剧《变形记》是今年阿那亚戏剧节演出剧目中口碑最佳的一部。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一场几乎没有差错的好戏:流畅的节奏,恰当的表演方式,可靠的文学依托,清晰的叙事,精准的批判性,足够真诚的共情……话剧《变形记》在前沿艺术与大众审美之间找到了一种非常舒适的位置,甚至偶尔对观众舒适感的逾越也谨慎地点到为止,让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冒犯,并且解读这种冒犯。作品切入现实社会的皮肉,却又保持着文学的冷静矜持;它引起观众的共情,又有所节制,使整部作品不至于向情节剧倾斜。但是我们很难将这部作品描述为一部杰出的戏剧。对于熟悉李建军的观众来说,《变形记》显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小说《变形记》的众多舞台改编中,李建军的这一版也不算出众。这部戏剧不具备一种公认的、本质性的缺陷,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到一种不足。
《变形记》剧照 摄影:潘晓楠
李建军的《变形记》在剧场中重构了卡夫卡的文本,原著中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当代中国的快递员。这样的解读太合适了:快递员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直接嵌入卡夫卡的文本,从头至尾没有一丝牵强,围绕这一内核建构的剧场艺术也处处表现恰当。这种恰当使作品呈现出成熟、流畅的风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正是过分的恰当削弱了剧场艺术的力量──原有的经典文本与当代文本之间、文本与表演之间没有呈现任何冲突,一切都太合适了。创作者使用新的叙事形式、新的表演方式、新的剧场理念来重构卡夫卡,重构的结果是使观众获得对双重文本的认知,这种创作方式已然取得成功;然而,在当代剧场艺术的语境中,重构中的龃龉和超越更能体现创作者的才华,在这一点上,李建军的《变形记》就显得有些保守了。李建军《变形记》前半段的表演方式容易使人误认为这部作品是以身体表演为核心的剧场艺术,与2018年日本静冈县舞台艺术中心(Shizuoka Performing Arts Center,SPAC)在中国大戏院的演出版本类似。四位演员在舞台上呈现出扭曲的身体,从演出一开始,就将变形这一主题物理性地表现出来。这与卡夫卡的写作方式一致,即人的异化直接表现为身体的变形,甚至面目全非。随着演出的推进,我们逐渐意识到,身体性表演在整个作品中执行得并不彻底,没有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与完整的审美体系,也不够具有说服力。例如扮演母亲与妹妹的两位女性演员的身体并没有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在台词不多的开场阶段缺乏辨识度。这些身体性表演并非精彩绝伦,但足以作为一种导引,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在舞台上表现人的异化。
而围绕这一主题建构的新文本才是作品的主体,也是这一版《变形记》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李建军《变形记》的舞台叙事与卡夫卡的原著构成一种平行文本: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这位格里高尔·萨姆沙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总会接触到的快递员,是他们之中极其普通的一位。我们也能轻易想象一位快递员的生活: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工作,苛刻的时间限制,高额罚款的风险,缺乏保障的劳务关系,简陋拥挤的生活环境,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位快递员的生活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对此心知肚明,但我们无能为力,有时甚至连一丝理解和宽容也顾不上。当代社会的正常生活就是对他人的艰难视而不见,并且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与之相关的利益中来,否则整个社会生活就没法运转下去。李建军在封闭的剧场空间里向观众展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剧场构成一种强迫的力量,使我们无法再逃避他人的艰难。这些悲剧也不再是关于现代生活的寓言,而是对当代社会的真实描画,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且参与其中。 《变形记》剧照 摄影:和平
《变形记》剧照 摄影:和平
如果创作者将关于整个快递员群体的观察和想象直接转变为一种原创叙事,那么这种叙事非常有可能呈现为一种臆测,透露出属于旁观者的狂妄自大;如果创作者在舞台上直接呈现对现实的观察,那么作品的风格就会转为与生活界限模糊的行为表演,像剧场团体草台班那些风格粗砺、态度鲜明的作品。在话剧《变形记》中,与原著平行的叙事使创作者在揭示现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关于这位快递员的一切都来自现实生活,除了他所经历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来自卡夫卡。与此同时,完善的文学依托也保证了剧场的艺术审美,当布满疤痕的底层生活被真实地再现出来时,作品的整体风格并未因此显得过于粗糙。这位快递员与卡夫卡笔下的旅行推销员构成了一组完美的平行线。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是上面的一条线──这位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前,生活还算体面,并且有一栋宽敞的大房子;快递员格里高尔则是下面那条线──他的住处狭窄拥挤,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工作时间对他的规训是以分和秒为单位的。人物在特定社会生活中的异化使两条线呈现出共同的延展方向,他们的异化由于相同的原理而发生,表现为相似的症状。他们是社会运转这套巨大齿轮中停不下来的零件,沉重的生活负担将灵魂挤出身体,只剩下一副盲目工作的躯壳。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以后没有表现出丝毫惊异,一心只想着如何拖着这具笨重的身体去上班;舞台上的格里高尔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冷冰冰的电子语音争分夺秒地提醒着他即将超时的危险。这种过去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电子人声如今完美地融入了现代生活,我们总能在小餐馆、便利店以及外卖员、快递员的身上听到相同的女性电子声。于是观众能感觉到,舞台上的这条平行线正是沿着我们生活的土地匍匐,而每个人都曾旁观过它的挣扎。平行线是和谐、美观的,通过一种坚定的秩序引起愉悦的审美。只要剧场观众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或是对其中的故事略知一二,就能从李建军的《变形记》中获得这种审美快感。旅行推销员与快递员,拉小提琴取悦客人的妹妹与直播间里唱歌的女主播,现代资本主义工作制度与更加严格的超时罚款制度……一切都巧妙地对上了。但过于和谐的当代阐释也造成了一种不足:当代文本与原著永远和谐共处,缺乏冲突。于是有观众认为,将格里高尔·萨姆沙呈现为一个快递员,这太肤浅了。这种看似苛刻的评论正是由于剧场文本与原著文本之间显得过于和谐造成的。整场演出显得非常顺畅,因为所有的批评和反思都已由卡夫卡代劳,在此基础上,剧场文本没有提供新的反思。我们不知道创作者的思路是以快递员的生活阐释卡夫卡的文本,还是套用卡夫卡的文本来表现快递员的生活,无论如何,新的文本极度依赖旧的思想内核,作品的文学依托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挪用。有时,创作者对原著文本的过度尊重甚至毫无必要,例如人物的名字是格里高尔·萨姆沙而非张三,但他明显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格里高尔·萨姆沙”是致敬,也是点缀和攀附,这个名字使作品在贴近现实的同时抓住了文学的格调,但这种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的方式显得有些刻意。剧场文本的种种处理方式当然不是不行,作品到此为止也已经成功了,只是缺少了一些思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冲突。熟悉当代剧场艺术的观众并不满足于创作者恰当、合理地诠释文本,我们还期待创作者迸发的灵感和激情,对原著文本的解构、篡改甚至背叛,只要这一切操作在创作者自己的舞台上能够成立。我们曾经将李建军和他的素人演员看作中国当代剧场艺术的革新者,也就更加期待创作者才华的体现。李建军的《变形记》既与原著文本贴合,又极度真实地刻画了现实。与顺畅却略显偷懒的剧场文本相比,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剧场呈现更富有能量。剧场艺术对现实的重构体现出强大的张力,一方面来自合适的表演和影像的配合,另一方面来自创作者尊重真实生活的赤子之心。正如前文所说,开头的表演不大令人满意,身体性表演略显做作,像是从别处借来的形式,既不够独特,又不够极致。即使这样,开头部分也不乏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例如,演员的身体缓慢滑过白色背景,留下棕色液体的痕迹,如同一只受伤的虫子勉强挣扎,将一些令人作呕的体液蹭到墙上。关于虫子的联想让人不那么愉快,而眼前的视觉形象又是通过柔软的、有灵魂的人类身体来呈现,整段表演引起的不适感就更加强烈了。正是由于表演带来了作用于感官的强烈刺激,剧场艺术才剥开了荒诞寓言的外壳,向观众揭示小说《变形记》中残忍的内核。这种创作思路非常合理。文学将内涵寓于文字之中,读者能反复回味,品读其中的深意;而剧场艺术引发当下的反应,是尖锐的,充满能量的,有冲突感的。在小说《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定,小说中大量主观视角的描述也因此显得异常冷静;舞台上的《变形记》在开场时同样是偏于冷静的,随着演出的展开,剧场氛围变得紧张,充满暴力和冲突,并渐渐趋向于一场黑色狂欢,所有的剧场元素都在这一过程中给人渐入佳境之感。对比小说,创作者没有对情节做出本质性的改动,表演的方式是实现剧场效果的关键,而影像的恰当配合同样功不可没。小说《变形记》中最激烈的情节是格里高尔的父亲向他掷苹果,“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小说中用在这段情节上的笔墨不多,但足以表现激烈、混乱的场景。父亲心意决绝,毫不留情,甚至让一只苹果嵌入格里高尔的后背。这段情节在演出中被着重渲染,创作者采取的策略简单却有效:将大量苹果掷向格里高尔。格里高尔的脸通过影像在屏幕上被放大,露出一副困惑而不安的神情,父亲凶狠地将苹果砸向这张脸,苹果碎裂四散。这段表演持续的时间比观众预期的更长,其目的并不是交代一段情节,而是使观众感受暴力,并且参与到暴力行为中来──享受这段表演的观众体验到与施暴者相同的发泄,对表演感到不安的观众在暴力重复的行为中体验到与受害者相同的压迫感。苹果撞击的清脆声响使我们清楚地感知父亲的决心和动作的力度,飞溅的苹果碎块落入观众席,让前排观众更直观地接受了一场暴力的洗礼。当代剧场艺术家热爱破坏水果和蔬菜,或许是因为这些食物完整的外观之下包含着充沛的汁水,如同人体遭受暴力之后喷涌而出的血液,最容易成为真实身体伤害的替代品,熟悉当代剧场艺术的观众不会对这些遭到破坏的苹果感到惊奇。难能可贵的是,李建军的苹果放大了小说《变形记》中残忍与暴力的一面,又利用不可撼动的原著文本将这一行为合理化,收敛了创作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表达欲,于是这段表演不会被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发泄,而更接近于集体狂欢。类似的狂欢氛围频繁地出现在节奏紧凑的后半段。例如,旧布料可能呼应了原著中格里高尔的藏身之处──为了不吓到家人,格里高尔用床单将自己蒙住。这种安静、隐秘的行为在舞台上表现为非常激烈的身体性表演,由格里高尔与他的家人们伴随着喧闹而愉快的音乐共同完成。虽然气氛与原著大相径庭,却与剧场契合,并且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共通的家庭关系。剧场中格里高尔与家人们的关系仍是虚伪的,但通过疯癫怪诞而非冷漠疏离来表现。影像与表演的配合非常出彩。拍摄快递员真实生活的纪录片出现在戏的开场部分,将这一位格里高尔的生活环境陈列在观众眼前。我们立刻意识到,剧场中呈现的不是那位旅行推销员,而是某一位曾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快递员。纪录片有效地实现了剧场中难以表达的环境描写,而社会环境的不同正是李建军的《变形记》与卡夫卡原著最重要的区别。演员脸部特写的实时影像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快递员格里高尔每天与形形色色的人短暂接触,这些与格里高尔萍水相逢的人也出现在剧中。创作者以这种方式塑造了同一社会环境中芸芸众生的群像,而这些个体也同样是被异化的。在这一段表演中,扮演格里高尔的演员快速地依次再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摄影机对准演员的脸,将影像投射到屏幕上,人们各异的精神样貌全部通过演员的脸表现出来。演员几乎没有表现出剧场中可观察的肢体动作,观众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屏幕上的特写上。影像的质量非常粗糙,但夸张的鱼眼镜头极具力量感,又如同安居家中的我们透过门镜一窥某位邻居的隐秘生活。此时,观众不得不认可演员精彩的表现,这种精彩并不一定证明演员演技高超,而是由于恰当的表演方式与恰当的影像相互配合。《变形记》剧照 摄影:潘晓楠
妹妹的扮演者的表演在这方面更加明显。这位演员在前半段的身体表演不够出彩,缺乏辨识度,用方言说台词的方式也缺乏说服力。在演出的后半段,妹妹在网络上直播唱歌取悦观众,与原著中妹妹拉小提琴取悦房客一致。这时,演员的脸部特写投射在屏幕上,我们突然发现这张脸是如此单纯、呆滞却楚楚动人。创作者完整地保留了妹妹唱歌的段落,在整个作品的结构上显得过长。观众们热爱妹妹的歌声,无论是刻意跑调的还是优美悦耳的,甚至集体挥舞起点亮了闪光灯的手机。我们可以将这段表演看作是可消费的娱乐,一种蓄意的媚俗,却不能否认它出现在《变形记》的舞台上非常自然,甚至带着模棱两可的讽刺意味。演员的脸部特写是实现剧场效果的关键。这是一位擅长用脸而非身体表演的演员,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一部作品指责演员的不完美,只要表演能以恰当的方式实现剧场性的表达就足够了。
影像的运用使剧场艺术能够选择性地呈现表演者的某些外观,这些外观的呈现足以制造强大的剧场效果。“在一切深刻的戏剧性之中,角色并不像有些人反复唠叨的那样,依靠心理分析而存在,角色是通过生物组织而存在的。演员的关键素质就是营造其生物组织:无论他是肥胖、蜡黄、胆小、汗津津还是爆裂,把人的物质状态抛上前台,也就是惹得我们犯恶心,这就是坚实的戏剧。”[1]正如罗密欧·卡斯特鲁奇曾经选择身体极度肥胖的演员来扮演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卡珊德拉,却选择极度瘦削的演员来扮演俄瑞斯忒斯,话剧《变形记》中演员的外观也因摄影机的参与而被恰当地呈现出来。格里高尔的扮演者看起来确实很像一只甲虫,这并不是因为他技巧性地模仿了甲虫的动作,而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给人一种与甲虫相似的坚实感。当鱼眼镜头拍摄演员的脸时,他的眼睛大得不可思议,并且灵活地旋转,像是某种长着许多复眼的昆虫。虽然甲虫不具有这种眼睛,但虫的意象仍然能使观众感觉到一种非人的怪异。一些观众声称在李建军的剧场中受到了冒犯,我却始终认为这冒犯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创作者选择了一个如此现实、如此沉重的主题,作品的内核也是犀利而严肃的,但外观却被精心打磨过,最粗糙的棱角被磨蚀了,成为文学,成为娱乐,成为景观。与此同时,创作者还没有放弃所有尖锐的表达,比如在结尾处直接向观众不客气地喊话,还彰显着一位前沿剧场艺术家的锐气。但在作品整体过于流畅的风格中,这些冒犯依旧显得有些轻浮。话剧《变形记》看似简陋粗糙──舞台空旷,影像粗糙,表演粗野──实际上,这部作品非常谨慎,剧场中的每一种行为都是恰当而合理的,是在原著文本中有迹可循的。作品的流畅自然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但我们仍然期待这样一部充满当代剧场艺术形式的作品呈现出更加锋利的姿态。
假如这部作品表现出更多的粗砺和锐气,那么阿那亚戏剧节将成为一个非常适合的演出平台。戏散后走出剧场,假模假式的欧式建筑和前来消费的游客便足以构成一个绝佳的讽刺场景。这时,剧场被重新搭建了,话剧《变形记》与所有心满意足的观众、受到冒犯的观众、漠不关心的游客一起,构成了一则崭新的异化寓言。[1]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论戏剧》,罗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55页。
本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仅做分享使用,不做商业用途,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留言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责编:易亿

 《变形记》剧照 摄影:和平
《变形记》剧照 摄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