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 0
- 0
分享
- 《戏剧》2021年第5期丨易杰:真实、暴力与仿真——论萨拉·凯恩戏剧中的客体
-
原创 2021-12-22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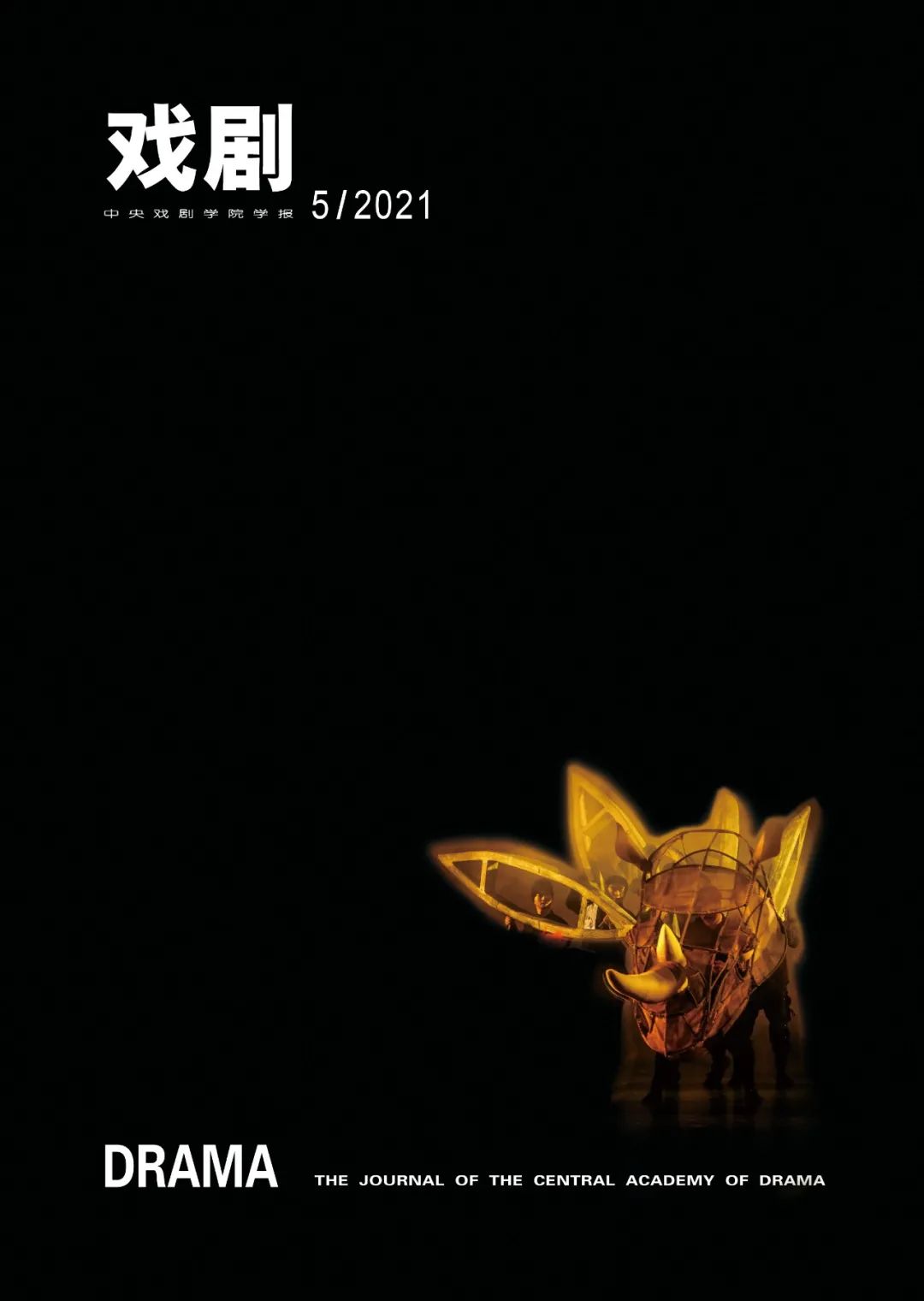
识别下方二维码查阅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电子版

真实、暴力与仿真
——论萨拉·凯恩戏剧中的客体
易 杰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讲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英国戏剧理论界通常将萨拉·凯恩的戏剧归类为“直面戏剧”。本文从共时到历时角度将萨拉·凯恩的戏剧与其他以暴力著称的英国戏剧进行分析比较,反对将她的戏剧归为“直面戏剧”概念。并从文化角度出发,揭示出萨拉·凯恩戏剧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戏剧客体。这个客体源自作家理想中的“真实”,但“真实”却是一个由媒体和消费社会所编码的符号与意义的后现代客体体系。
Sara Kane’s plays are mostly categorized as In-yer-face Theatre by the British critics. This paper compares Sara Kane's plays with other British plays known for violence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and oppo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her plays as In-yer-face Theatre. And after a cultural study, it reveals that it is the theatrical object makes Sara Kane’s plays the real difference. This object originates from the “real” in the writer's ideal, but “real” is a postmodern object system of symbols and meanings encoded by the media and consumer society.
关键词丨Keywords
萨拉·凯恩 直面戏剧 客体
Sara Kane, In-yer-face Theatre, Object
1995年萨拉·凯恩的处女作《摧毁》在英国皇家剧院上演。剧中呈现了性虐待、鸡奸、吸食眼珠,吃死婴等残暴形象,因而饱受评论界的攻击。之后她创作出另外四部戏剧,并于1999年自杀。英国学术界对她的评论和观点发生巨大变化,她被归为“直面戏剧”(In-yer-face Theatre)。并且,萨拉·凯恩已经成为继“愤怒”的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之后英国戏剧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她的戏剧风格背后模糊含混的意义引起戏剧界的关注。她从英国戏剧的“可怕小孩”变成了难以捉摸的萨拉·凯恩。她的前三部戏剧《摧毁》《菲德拉的爱》和《清洗》都是人类极端暴行的展示,而后期的两部作品《渴求》和《4.48精神崩溃》抛弃了戏剧叙事,拒绝线性、再现与语言的意义结构。
纵观凯恩的五部戏剧,可以说,她的整体风格不该被归为“直面戏剧”。她剧中的暴力既非美学的暴力主义,也非社会政治批判。她对真实的追求导致戏剧风格发生转向,但这种真实只是她的构想。通过对凯恩戏剧客体的研究可以发现,凯恩构想的“真实”是由大众媒体和消费社会所仿真的一个符码客体体系。真实已经被拟真取代。她前期戏剧对拟真“真实”的描述转向了后期隔绝内倾的自我表述。在一个被媒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的符号世界里,主体无力求真,只能困在虚假的客体陷阱。对于戏剧家和戏剧主人公,寻求真实的办法除了绝望的隔绝,也就只有死亡,才是摆脱符码客体秩序的唯一途径。
共时比较——萨拉·凯恩与“直面戏剧”
在前三部剧作《摧毁》《菲德拉的爱》和《清洗》公演之后,萨拉·凯恩俨然成为20世纪90年代“可怕小孩”的代表,她的剧作也被称为“直面戏剧”和新野蛮主义戏剧。亚利克斯·西尔兹(Alex Sierz)在自己书中《对峙剧场:英国戏剧的今天》( In-yer-face Theatre: British Drama Today)第一次系统地定义了“直面戏剧”:
台词粗俗肮脏,动作暴烈卑下,赤裸裸的色情与暴力;人物乖张,情节平淡且荒谬;观众被置于残暴、血腥、恐惧、恶心、焦虑相混杂的压抑情境之中,忍受力达到了极限,等等。从理论上讲,“对峙”一词传达出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艺术主张。它不反映时代的精神,不采用分离的艺术手法来使观众产生联想。只是展示生活中自然的存在,对暴行、犯罪、纵欲、妄想的直接揭示,带给观众惊愕与恐惧,从而让演员与观众共同来体验激情,体验梦魇般的狂妄。在“对峙剧场”里,生活与戏剧的界限没有了,生活中的一切隐私在舞台上暴露无遗,文明与宗教最深的禁忌被打破,生命中最基本的欲望—食欲和性欲—被公然揭示,人伦道德受到公然冒犯,观众的感官神经受到挑衅,而观众的接受与否变得无关紧要[1]。
从这些定义来看,直面戏剧似乎采用粗俗暴力和性的赤裸进行剧场视觉挑衅,让观众处于残暴、血腥、恐怖、恶心和焦虑的忍耐极限状态,用震惊和恐惧的方式使他们看到生活中自然存在的欲望、犯罪以及野蛮行为。而在萨拉·凯恩前期戏剧的表现方式中似乎存在西尔兹所说的“台词粗俗肮脏,动作暴烈卑下,赤裸裸的色情与暴力;人物乖张,情节平淡且荒谬”。但在语言上,“直面戏剧”的全部作品都以都市生活方式的通俗、诗性话语的亵渎性互文以及高度自我意识为标志。萨拉·凯恩与他们明显不同。在她的前两部戏里,几乎没有什么令人记忆深刻的话。在《摧毁》的前半部分里,对白非常简单。令人感到厌倦的猥亵,种族主义玩笑以及喋喋不休的辱骂,无法使人感到愉悦。如同邦德的《拯救》,对话就像一个迷宫。而在后半部分,语言已经失去了交谈的形式,被削减到对于暴力冗长而枯燥的紧张描述,最后甚至变成了动物般的呻吟和暴怒。对于伊恩的悲剧遭遇却不断地进行恐怖的叠加,没有节制。几乎没有戏剧家敢将邪恶的陈腐平庸进行得这么彻底。
同样被归于英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谓的“可怕小孩”还有大卫·艾尔德里奇(David Eldridge),乔·潘豪(Joe Penhall),西蒙·布洛克(Simon Block),帕特里克·马伯(Patrick Marber)和杰兹·巴特沃思(Jez Butterworth)。他们无论从戏剧目标和戏剧形式都与萨拉·凯恩没有什么相似。他们与“新锐派”(Britpop)以及“新不列颠艺术家”(New British Artists)风潮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戏剧形式还是传统观点,不过是重现20世纪60年代英国戏剧的戏剧设计和戏剧效果罢了。他们的风格都是社会现实主义,虽然与60年代戏剧有些细微差别和改变,但不同只在于他们带着品特式或者大卫·马麦特式的紧迫对白风格而已。他们的早期戏剧,主要集中于男性体验,“简单、社会性精确、完全否定史诗性或政治性遗产”[2](P377)。他们的戏剧展现的真实已经变成一种身份证。观众可能会被吸毒、性的坦白直率、诗意的猥亵以及“新”的、“直面戏剧”的内容所打动,从而在戏中人物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他们的戏剧很少能够触及基本的、伦理的和知觉的层面,剧本中的震惊效果也都是令观众能够认可的。他们希望培养新的观众而非责难他们。美学恐怖主义不是他们的兴趣。而萨拉·凯恩的同辈们如安东尼·尼尔森(Anthony Neilson)、马克·雷文希尔(Mark Ravenhill)或者菲利浦·里德雷(Philip Ridley)也是如此。雷文希尔的《购物和性交》的风格与特定的文化含义可能使一些观众不明就里,但从深层来说,却给很多观众以认同感。愉悦感是雷文希尔戏剧的美学主旨,虽然这种愉悦包含着极端和痛苦。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同性恋戏剧在形式上是明显的喜剧,对白带有王尔德风格的警句,结局令人恶心。
萨拉·凯恩的同辈们都在坚持或稍微改变固有的戏剧形式,但没有人想去挑战。雷文希尔戏剧的舞台冲击符号有烧死婴孩、舔肛门以及挖内脏,这与萨拉·凯恩戏剧中比比皆是的挖眼、断肢和肢体移植似乎也不具有互换性。在很多所谓的“直面戏剧”中,暴力是叙述性的,并且给人提供一种含糊的愉悦,构成戏剧道德体系的一部分。斯蒂夫·华尔特(Steve Walter)认为,这些剧作家的很多舞台暴力都来自于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当代电影暴力美学。昆汀认为暴力只是一种行动,是很多符号中的一种,没有任何道德后果,可以与任何其他行动或符号互换。
虽然萨拉·凯恩的暴力沉闷厚重,暴力场面频多,但她并不想创造一种昆汀·塔伦蒂诺式的暴力美学。邦德将昆汀的电影与《摧毁》作了一个比较:
她[萨拉·凯恩]能够渗透到每个人内心的深处,知道在那发生了什么。那不是只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它是我们联系外部现实的方式。如果你让外部世界进入你自己,那是混乱的和戏剧化的过程,而她触及到了这个过程,而人们不喜欢这个。在塔伦蒂诺和萨拉·凯恩之间有巨大的不同。两者都涉及混乱。一个说,混乱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必须进入到混乱中去找到我们自己。而另一个则说,混乱是一种伎俩,一种新的小发明—它是个花招。塔伦蒂诺赚到很多钱,萨拉·凯恩却杀死自己。[3](P25)
萨拉·凯恩本人也对昆汀的电影颇多质疑:“他不写暴力,他肯定也不写或不拍关于爱的电影……他的电影都是关于电影的手法,它们完全是自我指涉的,它们都指涉其他过去的电影—这是他们所做的一切”。[3](P25)她也在1996年德国汉堡上演的《摧毁》中发现了昆汀的影响。她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这个男人走上台……穿着时髦的皮夹克,油光的头发,墨镜将整个脸都遮住了—30多岁。我就想“哦,上帝,这个男人应该就是伊恩了”—这应该是个45岁的快死的人。我又想,“我在哪见过这个人物呢?”这是塔伦蒂诺。我的心都快爆了—我能听见我胸腔里的劈啪声!那在某种方式上说是很侮辱性的—我的作品被看作了我最憎恶流派的一部分。[3](P25)
她对汉堡的裸体演出也有关于“真实”的不满:
虽然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我的戏剧肯定是来自于一个戏剧传统,只是我在戏剧传统的最极端的一边。但是这些戏剧不是关于其他戏剧的,也不是关于戏剧呈现方法的,它们整体来说是关于爱、生存和希望的。而对我来说,这是极端不同的事情。在汉堡的演出中,凯特在晚上被强奸了,灯光都打开了,她躺在床上,完全赤裸着,双腿打开,全身都是血,对着伊恩发着牢骚。我看了之后只想死。我对导演说,“你知道她是在晚上被强奸的,你觉得她在一个强奸了自己的男人面前完全赤裸地躺在那有趣呢,可信呢,还是符合逻辑呢,或者有戏剧性呢?你不认为她应该比如说把自己盖上吗?”而且那与我对舞台上赤裸的感情无关。我以前也在舞台上裸体过,我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与在任何时刻的真实有关。[3](P25)
由此可见,萨拉·凯恩的戏剧不能被简单归类于“直面戏剧”。萨拉·凯恩不仅让人们直面现实生活中暴力、恐怖和野蛮,而且想通过舞台的暴力呈现让人们发现那些被隐藏的真实。她所理解的“真实”构成戏剧客体,对真实的追求成为主人公的戏剧行动。对“真实”的追求导致剧中主人公走向死亡。但她追求与再现的真实似乎仅限于暴力和死亡。她在剧中一再再现的客体现实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拟真。凯恩戏剧中极少数具有政治批判性的现实内容是《摧毁》中的波斯尼亚战争。她在写作过程中无意看到英国电视报道的战争现实,被其残酷性触动。于是开始描写丽兹酒店被炸弹摧毁,一位前南士兵插入戏剧行动,讲述并实施战争罪行,从而导致整一情节结构的分裂。问题在于,凯恩再现的战争现实是被英国媒体已经编码过的现实。在当代西方,媒体已将现实与真实分离。现实由大量的符号构成,使主体感官迷乱。这个迷乱的主体恰恰构成了《菲德拉的爱》中的王子希波吕托斯。而在《摧毁》结尾,具有特工与记者双重身份的主人公伊恩被士兵虐待,也具有了反讽意味,体现凯恩的“诗学正义”。
另外,凯恩所承袭的“一种戏剧传统”很有可能源自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这种戏剧传统是巴洛克式的。观众看到的是斯多亚式的主人公被不可预知的客体宇宙摧毁,并体现其“有尊严忍受”的美德。同时,凯恩也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詹姆斯派”的影响,但其重点在于对社会这一客体的政治批判。
历时比较——詹姆斯一世戏剧到新詹姆斯派
萨拉·凯恩戏剧的舞台暴力呈现让人想起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暴力的舞台形象令人发指,并且都尽力避免对人的行为进行心理分析或社会解释。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清晰可见,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戏剧受到巴洛克风格的影响,其客体世界由基督教教义和中世纪神秘主义所构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基督教哲学都已近衰落,实在论与唯名论围绕共相问题争论激烈,诺斯替主义对世相本源的解释重新抬头。诺斯替主义认为,世界的创造是盲目而骄傲的创造神堕落的错误结果,人是从神性世界到这个世界流浪的异乡人。
萨拉·凯恩戏剧中的人物都绝对质疑宗教。他们怀疑绝对价值和神,对他们来说,上帝已死,世界一片荒芜。除了形而上的“幽灵性”空间,神性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而他们唯一的信仰—真实,却将他们带向死亡。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与之类似,虽然戏剧主人公对宇宙的探索导致虚无与死亡,但绝对价值的存在不容置疑:
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尤其要求你悬置对绝对价值和巨大情感的存在的怀疑。他们要求你看宇宙中那些残暴的基本的遭遇。在一个宇宙中,神性对角色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有时也会令人担心的缺失。那些避免对人的行为进行心理或社会解释或将好坏简化至善与恶的戏剧不是有些令人鼓舞的东西吗?[3](P8)
萨拉·凯恩的戏剧与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客体世界的理解。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中的客体世界由超自然力量支配,萨拉·凯恩的客体世界却是由媒体和现代消费社会再现的符码支配。
萨拉·凯恩也被拿来与“新詹姆斯派”(New Jacobeans)的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和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进行比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批英国剧作家,由于其作品对舞台暴力的直接呈现,类似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作品,从而得到了“新詹姆斯派”的绰号,其中以爱德华·邦德、霍华德·布伦顿、霍华德·巴克(Howard Barker)和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s)等为代表。
邦德袭承道德批判式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暴力是社会政治问题。他认为,暴力是这个世界所有不公正的自然结果。所以他的作品里充满了触目惊心的暴力景象:《李尔》中“最新式的挖眼机”血腥的挖目场面;《拯救》中几个年轻人将一个婴儿活活用石头砸死;《大海》中洪水里等待救援的女人和孩子看着自己亲人的尸体在眼前漂泊;《傻瓜》中饥饿的农民抓起一个赤裸的肥胖牧师。这些场面都给观众带来巨大的震撼。
1965年,邦德第一次大胆地将暴力赤裸裸地展现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观众面前,一夜之间他“臭名昭著”,并开创了现代英国戏剧史上暴力戏剧的先河。也有评论家提出不同的观点,比如佩内洛普·吉列特(Penelope Gilliatt)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剧本身并不野蛮和残暴,野蛮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这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4](P15)
《拯救》中,邦德最想让人们看的不是杀婴的残暴场面,而是它后面的社会意义:这一冷漠的杀人行为是绝望社会的产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无所事事,靠福利维持生计,失去了任何精神和感情支柱,甚至丧失了人性。而戏中的暴力形象是为了表现那个把人们逼向麻木冷漠的社会。
《李尔》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血腥与暴力:两姐妹割去李尔忠实大臣沃林顿的舌头,踏烂他的双手,并用毛衣的织针扎破了他的耳膜。收留了李尔的掘墓工被士兵打死,他的妻子考狄利娅也被强暴。在狱中,李尔目睹了战败的大女儿被肢解以及二女儿被刺死的惨状,接着,自己也被一种新的刑具挖去双眼。
邦德是一个左翼剧作家,他的戏剧触及的是人的理性。他认为,暴力是当代社会的主题之一,它来自错误的社会道德观念。因此,要破除暴力,首要问题是要打破错误的观念,“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是一面镜子,你必须首先打破那面镜子然后将它重新组合,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他再塑了李尔这面“社会的镜子”,并让他成为自己阐述政治“暴力”的载体。
霍华德·布伦顿也是一个左翼剧作家,他的剧作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题的系列,另一类是对英国政治神话和文化神话的颠覆性“重写”。《罗马人在英国》是布伦顿第二部颠覆英国传统政治神话的剧作。剧中的暴力场面所引起的争议可以与邦德的《拯救》匹敌。此剧共有“12次屠杀和4次性暴力”[5](P80),以至于比林顿写道:“我不明白布伦顿为什么要这样刻意地表现暴力,一个爱尔兰人被吊在树上,割断了喉咙;一个罗马士兵把一个流浪汉切成了碎片;鲜血不停地从刺伤的腹部和大腿流出。可以肯定地说,该剧对暴力的表现程度是史无前例的。”[5](P80)在剧中,大多数暴力都发生在舞台后面,只有罗马士兵对马班的性暴力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极度残暴,令观众触目惊心。布伦顿通过这部戏剧的暴力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乐观自足的蒙昧无知,它是人们受到政治、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因素的误导并积淀形成的偏执认识。这种认识偏执往往体现为各种确定无疑的美丽的历史“神话”。其背后隐藏着对文明、人性的冷漠。
以上可见,“新詹姆斯派”基本是政治批判的剧作家,布莱希特的直接继承者。暴力是他们所批判或影射的社会问题,客体世界是出了问题的社会政治与体制。而萨拉·凯恩对政治与暴力的关系没有太多兴趣,她是一名笔触向内甚至“隔绝”的作家,她的作品似乎无意于当代英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以至于丹·里贝雷多(Dan Rebellato)和肯·厄本(Ken Urban)将她的戏剧描绘为“逃避现实者”和“虚无主义者”,认为戏剧中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并且反乌托邦的结局也无法使戏剧变成政治激进的作品。即使在最具社会政治内容的《摧毁》和《菲德拉的爱》里,她试图再现战争与皇室的残酷真实,但这种真实却是镜像化的。她的戏剧从过程到结尾最终还是关注人的存在状态和死亡,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在她后期的戏剧作品中,她甚至走向了隔绝和封闭。因此虽然她的舞台暴力呈现与邦德和布伦顿一样触目惊心,但却并非出于他们一样的政治道德使命。如同尼克切维奇所评价的那样,萨拉·凯恩的戏剧从来没有“使改变具有潜力”,因为她想象的世界“不是政治的,而是宿命的”。“他们在原型的层面上展现暴力,就好像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东西,而不像一个政治戏剧所反映的那样,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相反我们在看一个恐怖电影的戏剧类似物。邪恶和不幸是无处不在的,夺走无辜的受害者的生命。”[6]这些无处不在的邪恶和不幸就是萨拉·凯恩以及她的主人公所追求的真实。但这真实只是被拟真的客体,它将凯恩和她的主人公带向唯一的真实—死亡。
客体——后现代的符码地狱
客体概念的出现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有关。古代和中世纪哲学与神学的重点是本体论,研究世界因何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但文艺复兴充分肯定了人“权衡”宇宙的主体灵性,培根将哲学的对象从“验证上帝”转向“人的理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怀疑存在与感官的关系,肯定人类的思维。由此,主客二元的关系使认识论成为哲学核心,研究人类理性能否正确认识这个世界。这种转向使巴洛克戏剧的“人生是个大舞台”或“人生如梦”的概念在17世纪大行其道,其内涵在于认识世界,用虚幻消解现实本质。从皮兰德娄的戏剧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体现的也都是“认识论”问题。
萨拉·凯恩的客体世界也是“认识论”问题。她的客体不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不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由神所支配的宇宙,以及宇宙的偶然性所带来的巨大虚无。不是邦德的社会主义的真实可行性,也不仅指现代二元模式中客体概念—主体之外的现象世界。凯恩的客体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再现。
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戏剧提出“个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追寻“公共”身份占据戏剧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末,全球大众媒体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已经模糊了文化边界。国家或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概念受到挑战。在大众传播时代,“现实”本身越来越多地通过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媒介来体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文化与生活,图像与真实之间存在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文化图像成为符号,广泛出现在电视,广告,流行音乐,视频以及电脑网络中。这些符号构成了“真实”的社会现实。真实与真实的再现之间的区别开始消失,身份认同的可能性越来越难以实现。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拟真成为再现的本质。因此,七八十年代英国戏剧对“共同体”身份的追寻已被对个体身份的关注所取代。当“个人即政治”在70年代成为口号时,它表明了一个观点,即一些群体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文化主流之外,包括女性,同性恋,少数族裔等。然而,在90年代提出的“个体”,更多的是对自我的迷恋或对个人痴迷的自白,而不是代表受压迫或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声明。萨拉·凯恩的后期戏剧恰恰体现了这种变化,即前期戏剧中被符号化的仿真客体转移到后期戏剧中内倾的自我沉迷。
萨拉·凯恩戏剧中的客体是一个由媒体和消费社会所编码的符号与意义的体系。这个符号体系复制并模拟了真实,构成日常生活的客体。在其中,劳动被体制地位与劳动模式的符号取代,生产被消费取代,信仰被信誉取代,未来被怀旧取代,自我操控被远程遥控取代,深度被表层取代,整体被碎片取代,中心被块茎取代,宿命被任意偶然取代,主体被镜像取代,真实被符号取代。总而言之,人们生活在一个拟真的“超真实”中,景观、形象和符号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内容。这不仅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后现代奇观,也是萨拉·凯恩戏剧中的客体。
萨拉·凯恩戏剧的客体与其他作家戏剧中的对象世界不同,她的客体毫无理由地邪恶残酷,肆意任为,随时对戏剧中的角色主体发动突然的侵袭。存在于其中,就像生活在《黑客帝国》中楚门般的世界或者《盗梦空间》中的深层梦境。生存意味着存在于地狱般的客体世界。这个客体世界是可怕而变幻莫测的。《摧毁》中,一枚炮弹突然击中了利兹本该和平安宁的旅馆,突然将戏剧平稳空间的一致性打破。观众似乎被带到了未知的平行宇宙中,而来自未知客体的士兵对伊恩进行了残酷可怕的折磨。
萨拉·凯恩的五个戏剧既是对绝望的人生的描述,也是对于地狱般的客体的描述。就像她所说的:“我一直不断写作只是为了逃避地狱,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但从事情的另一端来看,当你们坐在席间一边看一边觉得那是对地狱最完美的表述时,我又感到这也许是值得的。”[7](P260)五个剧本中的场景都是她向观众展示的地狱:《摧毁》被炸弹摧毁的利兹豪华宾馆、《菲德拉的爱》里白金汉宫般的忒修斯的当代王宫、《清洗》中集中营似的大学、《渴求》中四个字母代表的人所处的地狱以及《4.48精神崩溃》中的精神病诊所。
萨拉·凯恩戏剧中地狱般的客体与萨特的地狱截然不同。萨特的中心是“他人即地狱”。在萨特的地狱里,人无法实现交流,永远处于孤独中,并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遭受挫折和失败。“自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在它的世界之外不仅有一个敌对的世界,而且还存在能够忍受同样困难并具有同样欲望的其他自我。这样,自我实现就增加了一层定义:它是逃离世界和他人的孤独。”[8](P94)
萨拉·凯恩的地狱远比萨特的地狱可怕。存在就是永远陷在不可避免、随时发生的死亡威胁的僵局中。人不仅永久陷在与他人的斗争之中,并且这个客体世界的自身是虚拟的。人们最可怕的敌人是客体,而非其他主体。
她想描述客体世界中主体的存在状态,但只有暴力带来的极端痛苦,才是真实的描述。她说:“有时我不得不遁入想象的地狱以避免落入现实的地狱。对我而言,最要紧的是牢记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件—以避免它们的发生。我宁愿在剧院里冒险下猛药而不愿生活在其中。”[3](P28)萨拉·凯恩用自己的敏锐向每个观众展示了每个人都曾经隐约感觉到的体验,她通过舞台形象迫使我们去面对所有这些体验。这些体验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客体世界已经凌驾于人类的存在之上,并使人类处于不可预知的危险之中。萨拉·凯恩的人物生活在一个未知的世界,命运不再是宿命,不再是欲望和自由所敌对的秩序,命运本身变成了一个强大而不可知的客体世界,这个世界的表象变成了由媒体所不断生产和自我重复的图像符号。人在这个世界中仍在努力寻找真实,却逐渐失去真实感。凯恩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客体世界中种种残酷暴力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个自我不断重复和复制的图像世界对人性的拒绝。
在萨拉·凯恩的前三部剧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戏剧中可怕而残暴的客体世界。在《摧毁》和《清洗》中,总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在掌控一切,随时向人类发动致命的报复。《摧毁》中利兹的豪华旅馆被突然而来的炸弹所摧毁,这未知的炸弹和波斯尼亚的士兵都来自不可知的客体。伊恩在被士兵残酷虐待后死去,却又处于不生不死的客体中。《清洗》中,所有人物都被廷克所代表的未知力量所窥视着、折磨着,廷克代表了那无法预知的客体力量。客体世界展示了它邪恶的一面,廷克和“幕后的声音”就是客体的具象。它体现了大众的意志,并对违反道德的爱情进行邪恶而疯狂的报复。在《清洗》的结尾,四肢被斩断的卡尔与格雷斯被互相移植了彼此的生殖器,这样的两个超性别的主体与《催毁》中的伊恩和凯特的状态非常相似,他们最后都被抛在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变幻莫测的客体世界中,寻求自我救赎和解脱,而他们之外的客体世界是一片充满老鼠尖叫的荒芜。
在《菲德拉的爱》里,希波吕托斯是一个当代的王子,他同样无法逃脱消费社会对他的侵蚀。皇室、性和礼仪都成为消费符号。他对神父的忏悔变成了他主持的神父对他的忏悔仪式。神父为希波吕托斯口交成为仪式的高潮,因为神父最终服膺于王子的宗教—真实。虽然希波吕托斯追求真实,但是图像为主宰的客体世界已经取代了真实的世界,一切都已经被媒体拟真。拟真创造了一种超真实。人们在超真实中只能迷失自己,永远无法找到真实。但希波吕托斯的唯一信仰就是真实,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因为只有死亡是唯一能找到真实的途径。当真实客体无法企及时,再现变得极为讽刺。
萨拉·凯恩后期的两部戏剧分别是《渴求》和《4.48精神崩溃》。这时她已经内向隔绝,贝克特式的痛苦折磨在剧中变得更加虚无—她彻底转向自我沉迷的自白。她否定戏剧叙事,放弃了线性、再现和语言的意义结构。《渴求》中四个角色继续探索欲望与绝望。四个人物C、M、B、A在一张桌后坐成一排,就像在公开辩论或受审一样。有时他们向听众讲话,有时是互相讲话,他们渴求毁坏自己的事物。对于凯恩和四个角色来说,爱是被渴求和不可能实现的,对于生者就是必须忍受的折磨,而死亡是唯一的出路。凯恩的最后一部作品《4.48精神崩溃》就像是一个破碎的梦,一首绝望和死亡的长诗。《4.48精神崩溃》是一个关于抑郁、无法舒缓的痛苦以及解脱的戏剧。剧名中的4.48是指凌晨四点四十八分,人们通常在这时生理和精神的错乱会达到极限,这就是一个人最可能自杀的时刻。从《摧毁》中对人类极端暴力的描述,到《4.48精神崩溃》中一个对存在绝望的内在个体,凯恩的戏剧经历了一个转向。她在1999年2月自杀,似乎是她作品的哲学结论的必然悲剧结果。
结语
综上所述,萨拉·凯恩无意于暴力的“直面戏剧”。她戏剧的核心是:在没有我们也一样发展,毫不在意我们判断和渴望的客体世界里,主体无能为力,个性毫无意义,被困在客体的陷阱中不得而出,随时面临着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这个地狱的最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对人的未知的威胁,而在于它与现实的分离。人生活在由媒体所创造的仿真的世界,找不到真实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切真实和意义价值都被媒体所不断生产和自我复制的图像所模拟了,乌托邦已经彻底解体为被摧毁和崩塌的世界,一切都被终结,没有上帝,没有彼岸世界,没有先验价值,没有历史,没有叙事,没有形而上学,没有价值和意义,没有生与死的界限,主体永远无法和客体最终一致。客体世界甚至比地狱更加可怕,因为人们已经永远迷失在虚拟的真实中了。在这个拟真世界里,唯一的出路和绝对的真实只有一个:死亡。死亡虽然可怕,但相对于存在,却是唯一一个通向真实的出路。这是萨拉·凯恩戏剧的独特之处,也是萨拉·凯恩走向自杀这一必然结局的终极原因。在客体的符码统治中,死亡的地位非常重要:“或许死亡并且单是死亡,死亡的可逆性,属于一种比符码更为高级的秩序。唯有符号化的失序才能导致符码的中断。”[9](P163)
参考文献
[1]万俊. 萨拉·凯恩和“对峙剧场”[J].戏剧, 2006(1).
[2]WATERS Steve.Sarah Kane: From Terror to Trauma[M]// M. Luckhurst (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British and Irish Drama .Oxford: Blackwell, 2006.
[3]SAUNDERS, GRAHAM. “Love Me or Kill Me”: Sarah Kane and the Theatre of Extremes[M].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2.
[4]PHILIP Roberts, File on Bond[M]. London: Menthuen, 1985.
[5]王岚,陈红薇. 当代英国戏剧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NIKCEVIC, SANJA. British Brutalism, the “New European Drama,” and the Role of the Director[J].New Theatre Quarterly 21.3 (Aug. 2005).
[7]萨拉·凯恩. 萨拉·凯恩戏剧集[M].胡开奇,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雷蒙·威廉斯 .现代悲剧[M].丁尔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乔治·瑞泽尔. 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投稿须知
《戏剧》是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艺术类学术期刊。本刊试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者来稿须标明以下几点:
1.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位。
2.基金项目(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3.中文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篇幅为150-200字。
4.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大致对应,长度为80个英文单词左右。
5.中文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6.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大体对应。
7.注释:用于对文章正文作补充论说的文字,采用页下注的形式,注号用“①、②、③……”
8.参考文献:用于说明引文的出处,采用文末注的形式。
(1)注号:用“[1]、[2]、[3]……”凡出处相同的参考文献,第一 次出现时依 顺序用注号,以后再出现时,一直用这个号,并在注号后用圆 括号()标出页码。对于只引用一次的参考文献,页码同样标在注号之后。文末依次排列参考文 献时不再标示页码。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
a.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M].
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外文版专著、期刊、论文集、报纸等: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姓在前,名在后,之间用逗号隔开,字母全部大写。书名、刊名用黑体。尽量避免中文与外文混用。
来稿通常不超过10000字。请在来稿上标明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电话,发送至学报社电子信箱:xuebao@zhongxi.cn。打印稿须附电子文本光盘。请勿一稿多投,来稿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录用或修改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发现有一稿多投或剽窃现象,对我刊造成损失,我刊将在3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投稿。来稿一般不退,也不奉告评审意见,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
《戏剧》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也未单独开设任何形式的网页、网站。同时,中央戏剧学院官微上将选登已刊发文章。
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欢迎关注中华戏剧学刊联盟刊物公众号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

《戏曲研究》

《戏曲与俗文学》

《中华戏曲》

《戏剧与影视评论》
图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社



-
阅读原文
*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数艺网立场转载须知
- 本文内容由数艺网收录采集自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 ,并经数艺网进行了排版优化。转载此文章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标注“作者”、“来源:数艺网” 并附上本页链接: 如您不希望被数艺网所收录,感觉到侵犯到了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数艺网,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处理或删除。













